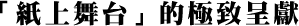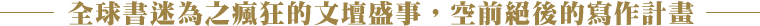
1616年,莎士比亞離開了人世
400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從他筆下的人物中照見自己
為紀念莎翁逝世400週年,英國藍燈書屋特別籌畫三年的「挑戰莎士比亞」書系
邀集當今文壇呼風喚雨的七位小說名家接下戰帖
為21世紀讀者搭起「紙上舞台」
以現代時空、全新觀點、小說形式,重新演繹莎士比亞的雋永經典

細說創作緣由
我選擇挑戰《冬天的故事》,是因為這齣劇三十多年來對我一直有很私人的意義──它是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文字作品。《冬天的故事》寫的是棄兒,而我自己就是個棄兒。這齣劇寫的是寬恕,寫一個充滿未來各種可能的世界,也寫寬恕與未來是如何彼此牽繫。時間終能倒轉。
溫特森是英國當代公認極具代表性的作家,1985年以具有濃厚自傳色彩的處女作《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一舉奪下英國惠特布雷小說獎,由她親自改編的同名BBC影集也大獲好評,囊括各個國際大獎,作風大膽、離經叛道的溫特森,自此一躍成為英國文壇最耀眼的新秀。英國BBC電視台曾舉辦「女性分水嶺小說」票選活動,溫特森有3本小說獲得提名,是入選作品最多的當代小說家。她的作品已翻譯為32國語言,2006年以其傑出的文學成就獲頒大英帝國勳章。溫特森自剖,寫作歷程一直緊扣著「愛」這個主題。她曾寫道:「『愛』是一個難懂的字,一切都從這個字開始,我們也總是回到這裡。愛。愛的匱乏。愛的可能性。」歸根究柢,《冬天的故事》探討的正是「愛」的救贖力量。溫特森認為這部劇作就像她的護身符,曾在苦澀的成長歲月撫慰她的心靈。
《冬天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失落、懊悔、寬恕,以及「時間」的故事,溫特森巧手將「時間」轉化為現代電玩中的元素,並以她大膽又獨具詩意的筆、對於愛與悲傷深刻的洞見,創造了獨一無二的全新作品。即使與原作相隔四百年時空,我們仍舊受困於同樣的執著,只待「時間」的神祕力量插手,才能帶來寬恕的契機,讓人重獲自由。

珍奈.溫特森
Jeanette Winterson
挑戰《冬天的故事》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挑戰《暴風雨》

安.泰勒
Anne Tyler
挑戰《馴悍記》


霍華.傑可布森
Howard Jacobson
挑戰《威尼斯商人》
崔西.雪佛蘭
Tracy Chevalier
挑戰《奧賽羅》


尤.奈斯博
Jo Nesbo
挑戰《馬克白》
吉莉安.弗琳
Gillian Flynn
挑戰《哈姆雷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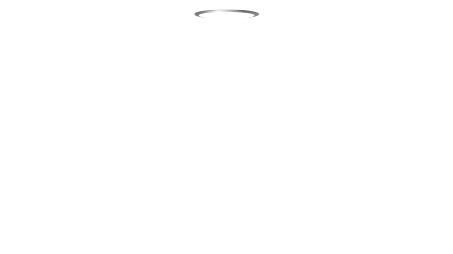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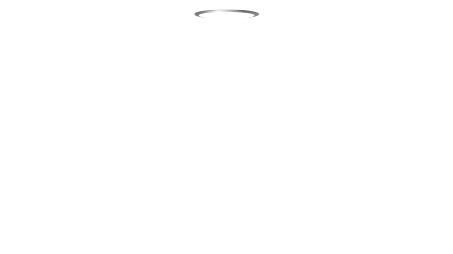

她坦言《暴風雨》是她最喜愛的莎翁作品,這場挑戰為創作生涯注入了全新能量。而她結合了過往橫跨奇幻、科幻與詩的創作經驗,傾盡畢生功力穿越驚濤駭浪的《暴風雨》,讓劇中的魔幻色彩徹底轉化為現代語言。

「罪惡的本質」是奈斯博所有創作的核心,加上他喜愛緊抓相對單純的故事架構做發揮,因此很快便選定挑戰《馬克白》。

雪佛蘭出生於美國華盛頓,與丈夫和孩子長期住在英國倫敦,卻因自己的美國口音而始終難以融入,對於莎翁筆下奧賽羅身為「異鄉人」的心境深感共鳴,決定勇敢直視心中的恐懼,接下戰帖。

她認為所有故事的詮釋,必然都有當事人不曾言說的「另一個版本」。《馴悍記》是莎翁筆下頗具爭議的作品,但她將以一雙洞悉世情的慧眼,挖掘出故事中未被看見的隱藏面向。

他選定挑戰《威尼斯商人》,卻因自己身為猶太裔而遭友人嘲笑「真是瘋了!」,但他不願錯過這場挑戰莎翁的文壇盛事,堅持從獨一無二的角度,讓劇中的猶太人夏洛克發出不同的聲音。

弗琳刻畫黑暗人性的功力有目共睹,她坦言:「我接下挑戰,正是因為莎士比亞的名號令我膽寒!」在藍燈書屋規畫這套書系的三年期間,莎翁筆下的悲劇遲遲沒有作家願意答允挑戰,直到吉莉安.弗琳與《哈姆雷特》的組合正式公開,全球書迷的期待指數也達到最高點!

林奕華.韓良憶.鴻鴻.李屏瑤.童偉格.梁文菁.何一梵.王耿瑜 感動推薦、耿一偉〈紙上演後座談〉專文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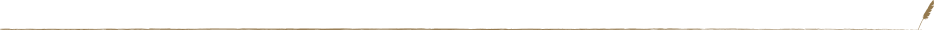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如果說莎士比亞以《冬天的故事》重新審視《奧賽羅》,將背叛、嫉妒與狂暴,導引成可能的寬恕,《時間的空隙》將空間撐得更大些,靈巧地張開羽翼,舉重若輕地說完一場失物招領的故事。──李屏瑤(劇作家、文字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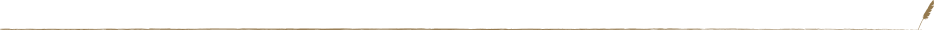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時間的空隙》圈點「寬恕」,這一莎士比亞晚期劇作的共同主題,而將《冬天的故事》這一以陰森氛圍吸引觀眾的通俗喜劇,改寫為較切合當代語境與心理邏輯的小說……明快,富巧思,向來是溫特森的書寫特色,而此作,可能是她最明亮且溫暖的一部小說,確認了互解的必要,與人們彼此療癒的可能。──童偉格(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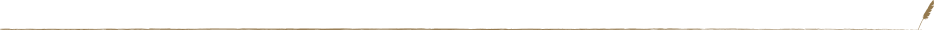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冬天的故事》或許是莎士比亞劇作裡,最難以處理的劇本,推敲起來疑點處處、不易拿捏。例如:上下半場十六年間的差距、被熊追趕著下場的場景、以「時間」為名的角色等等,更不提雕像起死回生的最後一幕,真要演出此劇,每項細節都讓人傷透腦筋……溫特森將故事場景代換至當代的倫敦、巴黎與紐澳良,緊密扣著莎劇情節發展,還不著痕跡地以其擅長的同志書寫,豐厚並合理化角色的心理動機,喜愛原劇者不容錯過。──梁文菁(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台灣莎士比亞學會秘書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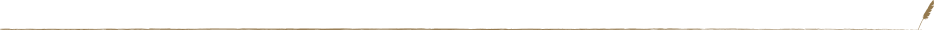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從一個作家的筆下到另一個作家的鍵盤上,故事總是變形的,可是在《時間的空隙》中,輕快的語調捲起了龐然的深沉與憂傷。聰明的評論或許會這樣聲明:這與莎士比亞無關了。但在這個現代小說的變體裏,莎士比亞卻是被小心翼翼地維護:敘事拆散了,角色重新鍛造,但在與原作呼應的空隙中,溫特森掘出了埋在其間的陰暗。──何一梵(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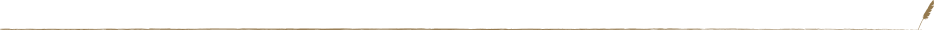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這是個關於挽回的故事。同樣以嫉妒為主題,莎翁的《奧塞羅》讓大錯鑄成,他晚年的《冬天的故事》卻用了傳奇的筆法,讓人生因愚蠢而失去的一切,有了挽回的契機。然而當代還有傳奇的可能?珍奈.溫特森舉證歷歷:這是一個有《超人》《回到未來》、也有電玩遊戲的時代。兩位男主角還曾經「基」情熾烈。時空移轉,人的愚昧與善良、執迷與荒謬不改,讓這則傳奇,在濃烈的當代都會氣息中,以無比的活力再現。──鴻鴻(詩人、導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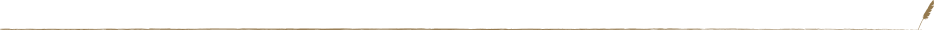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時間不等人,但人可以把時間種出時間,舊的故事便有了新的啟發。經典是最有養份的泥土,把它耙鬆的方法,是借用每個人的生活,因為能把經典解出新意,從來不是你去讀它,卻是它來讀你。莎士比亞了解我的方式是,通過我在與他照面時所發現的似曾相識,這句話我在什麼時候聽過,想過,說過?他幫助了一個人從讀者變成作者:創作,使生命不斷的自我超越,由自己發現自己開始。──林奕華(導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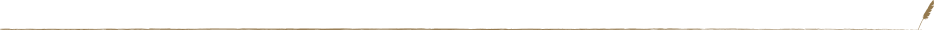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想像那個在大學畢業,就進入劇場打工,書包裡始終擺著《冬天的故事》並帶著覺察的第三隻眼,時時俯瞰自己生命軌跡的珍奈.溫特森……想像那個在成人之後,得知自己是個被領養的小孩,終其一生在尋找生母,並以書寫,面對傷口、失落和愛的中年女人。「我抱著寶寶在街上走,掉進了時間的空隙──某個時間,和另一個時間,在這道空隙裡,化為同時。」想像那個總是在富有隱喻的童話、神話和網路、電玩中來去自如,原來生命靈數5的她,「自由」是她一輩子的功課。──王耿瑜(電影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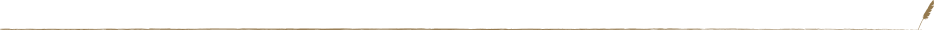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珍奈.溫特森勇敢接下改寫《冬天的故事》這個艱鉅挑戰,激盪出一部閃閃發光的小說……她極為擅長捕捉人們未曾言說的心緒,以深具力量的抒情語言,創造了書中角色迷人的觀點,也徹底讓小說以其獨特的文學形式,揭露了劇場演員的內心世界。雖然站在莎翁的陰影之下(現代作家誰不是呢?),《時間的空隙》本身就是個精采的當代故事,讓人掩卷時心滿意足。──《紐約時報》書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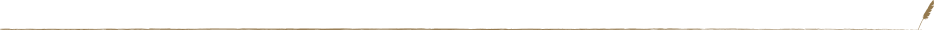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溫特森的文學舞台一如莎翁的劇院舞台,充滿令人嘆服的奇景。──《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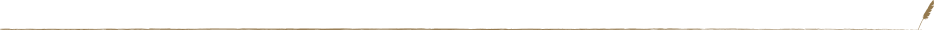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一頁頁讀來都是如此真實、充滿了無垠的想像力,你不可能不迷上這部作品。──《倫敦標準晚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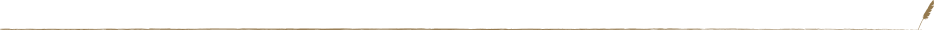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溫特森巧筆一揮,莎翁筆下的角色便換上了當代衣裳,懸疑張力貫串全書。這是「挑戰莎士比亞」系列極為成功的開場,也預告了接下來更多精采的文學旅程。──《每日快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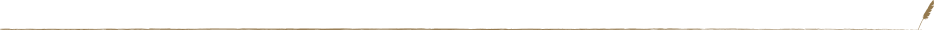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作者以精湛筆力將多層次的敘事與主題交織在一起,閱讀過程有如聆聽巴哈的前奏曲與賦格……極其精巧、扣人心弦且具有感染力,其細膩層次值得再三品味。──英國《週日郵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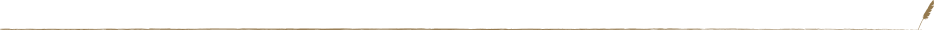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這部向莎翁劇作《冬天的故事》致敬的小說,有著獨特的迷人氣息、輕快的節奏,而且機智又慧黠。除了情節上忠於莎翁原劇,還在重重挑戰之下寫出了讓人無法釋卷的故事,令人讚嘆、深具娛樂性又優雅,真是了不起的成就!──《衛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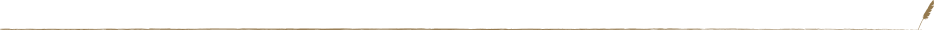
挑戰莎士比亞:一場空前絕後的寫作計畫!
2016向莎翁致敬的筆尖對決,強打首發《時間的空隙》

似水之月
我今晚看見怪到極點的事。
我在回家的路上,外面是窒熱的夜。每年這時候就是這樣,皮膚總罩著汗珠的光,上衣永遠乾不了。我在平常固定演奏的那個酒吧彈鋼琴,只是今晚的客人沒半個想走,所以即使我想準時下班,最後還是比平常晚收工。我兒子說會開車來載我,卻一直不見他人影。
我在回家的路上,大概已是清晨兩點左右,冰涼的啤酒瓶,在我手裡慢慢有了溫度。是,我知道不該在街上喝酒,不過,管他呢,老子在酒吧不忙時負責倒酒,酒吧一忙就得彈鋼琴,這樣連幹了九小時活,喝一瓶不為過吧。有現場演奏,大夥兒就會喝得比較多,這是事實。
我在回家的路上,結果這天氣說變就變,傾盆大雨如冰塊當頭澆下(還真的是冰)──高爾夫球大小的冰雹,像石頭一樣硬。街道早吸飽了這一天、這一週、這個月、這一整季的熱,冰雹一落地,便好似把大堆冰塊倒進滾燙的油鍋,於是這正常的自然現象,反倒變得不像從天而降,而是從街上緩緩升起的東西。冰雹在我腳邊爆開無數碎片,我忙著左躲右閃,一見樓房有點遮蔽的大門口就去暫避。冰雹落地激起的嘶嘶水霧,害我連自己的腳也看不見。最後我終於爬上教堂前的階梯,這才有了一、兩分鐘空檔,擺脫腳下那層白霧。這時我早已成了落水狗。口袋裡的鈔票全黏在一起,濕漉漉的髮緊貼著頭。我擦去眼中的雨水。雨的淚。我太太過世都一年了,找遮風避雨之處又有何益,不如回家吧。
於是我決定抄近路。我平常不喜歡走這條近路,因為會碰上「棄兒箱」。
那是醫院一年前裝的。那時我每天都去醫院探望太太,也就每天看著工人忙進忙出,灌漿做混凝土外牆,在牆內放進鐵箱,又裝上氣密窗,接上暖氣、電燈、警鈴等等。有個工人不願做下去,我猜他大概是覺得這樣不對、不道德。這是這時代的某種徵兆吧。只是這時代的徵兆實在太多,若是想一一解讀,只怕會心碎而亡。
那箱子牢固又溫暖。要是有人把寶寶放進去,關上箱門,醫院的警鈴就會響,不多久便會有護士下樓來,這中間的空檔,正好能讓做母親的離去──那箱子就裝在街角。她隨即消失無蹤。
我就看過一次,還追在她後面,大喊:「小姐!」她回過身,望我。那一秒,全世界為之凝結──下一秒啟動,她已遠去。
我走回箱邊,箱中空空如也。我太太幾天後走了,所以後來我再也沒從那條路回家。
「棄兒箱」是有歷史的。故事不都有歷史嗎?你自以為活在當下,過去卻跟在背後,如影隨形。
後來我做了點功課。歐洲早在中世紀某個時期就有「棄兒箱」了,他們稱之為「棄兒之輪」──因為那是修女院或修道院的一扇圓窗,你可以把寶寶從窗外放進去,期盼上帝看顧。
你也可以把寶寶裹一裹放在森林裡,讓狗啊狼啊去養。你就此離去,沒為寶寶留名,卻留下讓故事開始的契機。
有輛車疾駛而過,把路上的水濺了我一身,是嫌我不夠濕還是怎樣?這王八蛋。結果車停了下來──原來是我兒子克羅。我坐進車內,他遞上毛巾,我連忙擦了把臉,很慶幸終於得救,也突然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我們駛過幾條街,聽著車上的收音機。氣象報告講的盡是些怪事:超級月亮、海上巨浪、大水淹沒河堤。別出門、留在屋內。這不是卡崔娜颶風,但也不是適合出門晃蕩的晚上。停在馬路兩旁的車,輪子已經有一半泡在水裡。
然後我們就看到了。
我們前方有輛BMW 6系列的黑車,對著牆一頭撞成稀爛,兩邊車門大開。後面還有輛小破車,車尾已經凹陷。兩個混混把一個男的打倒在地。我兒子上半身壓在喇叭上朝他們直衝,一邊放下車窗大吼:「搞屁啊?搞屁啊!」就在他全速進攻之際,有個混混朝我們開了一槍,想打爆前輪。我兒子方向盤一扭,車便撞上路緣。那兩人跳進BMW發動,車身沿著牆狠狠擦過,把那輛小破車頂到對街。被打趴的那個男的仍倒在地上,全身高檔西裝,人大概六十歲左右,流著血,雨把他臉上的血沖得一地。他嘴動了動,我在他身邊跪下,卻只見他兩眼圓睜,死了。
我兒子望著我(我畢竟是他爸)──我們該怎麼辦?接著,我們都聽見遠方響起警笛,像另一個星球的聲音。
「別碰他。」我對兒子說。「倒車。」
「我們應該等警察來。」
我搖頭。
我們在街角把打爆的前輪七手八腳裝回去,沿著會經過醫院的那條路慢慢開。有輛救護車駛出急診室的車庫。
「我得把輪胎換了。」 「
你停到醫院停車場去。」 「
我們應該把剛剛看到的事跟警察說。」
「他人都死了。」
我兒子把車停好,到車後去拿換輪胎的工具。有那麼一會兒,渾身濕透的我,就這麼坐在濕透的座位上。醫院刺眼的燈光透過車窗朝我當頭劈來。我討厭這間醫院。我太太死後,我就是這樣坐在車裡,透過擋風玻璃朝外望,只是什麼也進不了眼裡。一天過去,換上黑夜,什麼也沒變,因為一切都變了。
我下了車。我兒子把車尾用千斤頂頂起來,我們合力取下輪胎。他已經先把備胎從後車廂拿出來放好。我伸手在前輪的破損處摸索,拔出那顆子彈。無論如何我們都用不著這玩意兒。我拿著子彈,打算把它往路邊深不見底的排水溝一扔。
就在那時,我看到了。那燈。
「棄兒箱」的燈亮了。
我不知怎地有種感覺,這一切都有關連──BMW、破車、死掉的男人、嬰兒。
因為那裡真的有個嬰兒。
我走向棄兒箱,整個人成了慢動作。那娃兒睡得正沉,吮著拇指。還沒人來。為什麼還沒人來?
我這才發現自己一直握著撬胎棒而不自覺;我動手撬開那箱子而不自覺。易如反掌。我抱起那嬰兒,她耀眼似星辰。
* * *
夕陽西沉,求主與我同住;
黑暗漸深,求主與我同住;
求助無門,安慰也無覓處,
懇求助人之神與我同住。
今早的會眾聲勢浩大,教堂裡塞了大約兩千人。外面淹大水,顯然動搖不了大家上教堂的決心。牧師說:「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這段話出自《聖經》中的《雅歌》。我們唱自己熟的歌。
「救恩堂」起先只是簡陋的小木屋,後來漸漸擴大為房舍,再變成一個小鎮的規模。會眾大多是黑人,也有白人。白人不太容易信「信靠某事」這一套,又很拘泥某些細節,像七天創世啦、耶穌復活之類。我自己是不管這些啦。假如沒有上帝,我死了也不會糟到哪裡去,反正死都死了。假如有上帝,嗯,那好,我懂你意思──那你說說,這上帝到底在哪兒?
我是不曉得上帝在哪兒,可我覺得上帝知道我在哪兒。祂有世上第一款全球通用的應用程式。「搜尋薛普」。
正是在下。薛普。
我和兒子克羅相依為命,過著低調的生活。他今年二十歲,是在這兒生的。他媽是加拿大人,外公外婆則是印度裔。而我呢,我想我是坐奴隸船來的──好啦,坐船的不是我,但我DNA裡仍有非洲的印記。我們現在住在新波希米亞,從前是法國殖民地,種了大片甘蔗,有殖民風的大宅院,集美好與驚悚於一身。有觀光客最喜歡看的鑄鐵樓梯欄杆;有漆成粉紅、黃、藍等色的十八世紀小屋小樓。店家向街的那面有木造大門與窗框,嵌著外凸的圓弧形大片玻璃。小巷裡則是一條條漆黑的通道,通往男性尋歡之地。
還有河。很寬的河,寬得像未來曾有的模樣。還有音樂──總有女人在某處唱著歌;總有彈班鳩琴的老男人。也可能是收銀機旁的女生,搖著兩支沙鈴。或許是讓你想起母親的小提琴聲;或許是你寧願遺忘的曲調。記憶是什麼?記憶無非是與往昔痛苦的爭執。
我看別人寫過,身體每七年就會自己再造。每個細胞都會,連骨骼都會像珊瑚自行再生。那,我們為什麼會記得理應如煙的往事?每道傷痕,每回屈辱,意義究竟何在?美好時光若已遠颺,又何必記住不忘?我愛妳,我想妳,而妳已不在人世。
「薛普!薛普?」是牧師。嗯,謝謝你,我很好。對啊,昨晚還真的有夠嗆。上帝對人類的無數罪行自有審判。這位牧師相信這點嗎?不相信。他相信的是全球暖化效應。上帝用不著懲罰我們,我們自己來就行了,所以我們才需要原諒。人類根本不了解「原諒」。「原諒」,是個詞,就像「老虎」──我們都看過老虎的影片,事實也證明老虎存在,但很少有人真的近距離看過牠生龍活虎的模樣,也少有人真正了解牠的本性。
我就無法原諒自己做的事……
有一晚,夜已深,一片死寂的大半夜──人說「『死』寂」不是沒道理。我把躺在病床上的太太活活悶死。她渾身無力;我壯如蠻牛。她得靠氧氣才能活,而我,拿開她的氧氣面罩,雙手摀住她口鼻,請耶穌來帶她走。祂真的辦到了。
病床旁的監視器嗶嗶叫,我知道很快就會有人來,也不在乎這麼做的後果。可是沒有人來,最後我還得跑出去找人──這醫院護士太少,病人太多。出了這種事,他們也不知該怪誰──雖然我很肯定,他們覺得是我幹的。我們幫我太太全身蓋上床單,等醫生終於來了,他寫的死因是「呼吸衰竭」。 做了這件事,我不後悔,卻難以釋懷。我做了正確的事,卻是錯的。
「你為了正當的理由,做了錯事。」牧師如是說,這卻正是我們意見不和之處。乍看之下,我們講的話不過是把幾個字的位置換一換,但這中間的差異可大了。他是說,取人性命是錯的,但我這麼做是為了免她受苦;我則堅信取她性命是對的,我們是夫妻,本為一體,只是我這麼做的理由是錯的,我沒多久便明白了。我出手不是想終止她的痛,是想了結我自己的苦。
「別再想了,薛普。」牧師說。
我從教堂出來後便回家。兒子在看電視。寶寶醒著,不吵不鬧,一雙大眼直瞅著天花板,那上面是陽光透過百葉窗畫出的條條黑影。我抱起她,逕自開門出去,往醫院走。寶寶暖烘烘的很好抱,比我兒子出生時還輕。那時我們夫妻倆剛搬到新波希米亞,對一切深信不疑──對世界、對未來、對上帝、和平與愛,還有,最重要的,我們相信彼此。
我抱著寶寶在街上走,掉進了時間的空隙──某個時間,和另一個時間,在這道空隙裡,化為同時。我身軀變得挺拔,跨的步伐變大。我是個娶了漂亮姑娘的青年,忽然間兩人就當了爸媽。「托著寶寶的頭。」她叮囑著,我抱起他,用手捧著他的命。
他出生後那一整週,我們完全下不了床,吃睡都在床上,中間躺著我倆的寶寶。那整整七天,我們就只是目不轉睛望著他。我倆創造了他。無需技巧,不必訓練,沒有大學文憑,不靠科學經費,我們就製造出一個人。我倆居然能在這個亂糟糟的瘋狂世界做出人來,這是什麼世界?
別走啊。
你說什麼?先生?
對不起,我剛剛胡思亂想,亂講話。
好漂亮的寶寶。
謝謝。
女人走了。我這才驚覺自己站在人來人往的大街上,抱著熟睡的寶寶自言自語。但我不是自言自語,我是對妳說話。這習慣還是沒改。我總愛對妳說話。別走啊。
你懂我剛剛形容的「記憶」嗎?我太太已經不在,世上沒這個人了。她的護照早已註銷,銀行帳號也關了,她的衣服現在穿在別人身上,但我腦裡全是她。倘若她從未到這世上走一遭,而我腦裡全是她,應該會有人說我失心瘋,把我關起來才對。我就是走不出傷痛。
我發現,「傷痛」的意思是「和已經不在的人同住」。
妳在何方?
摩托車引擎呼嘯。來往車輛放下車窗,車內放著收音機。孩子玩滑板。有隻狗兒在叫。送貨卡車忙著卸貨。兩個女的在人行道上吵架。人人都在講手機。有個男的站在箱子上大喊,「一件不留」。
這我沒問題。都拿走吧。車、人、拍賣的東西。把這一切清光,化為我腳下塵土頭上青空。聲音關掉,畫面全白。我倆之間空無一物。今晚我是否會見妳向我走來?如妳慣常的模樣,如我倆下班回家精疲力盡的模樣?我們抬眼,望見彼此,先是隔得好遠,然後就在跟前?妳的能量再次化為人形,妳的愛是原子的形狀。
「沒什麼。」她知道自己來日無多時,這麼說。
沒什麼?這樣的話,天不算什麼,地不算什麼,妳的身體不算什麼,我們做愛也不算什麼……
她搖頭。「我生命中最不要緊的就是死了。有差嗎?反正我也不會在了。」
「我會在。」我說。
「殘忍就殘忍在這兒。」她說。「假如我可以為了你拖著生不如死,我當然也願意。」
「關門大拍賣!一件不留!」
都過去了。
我來到醫院那條街,看見了棄兒箱。只是這時我懷裡的寶寶醒了,我感覺得到她在動。我們對望著,她骨碌碌轉動的藍色雙眸,尋覓著我陰鬱的眼,又舉起一朵小花般的手,觸著我臉上扎手的鬍碴。
在我,與我即將越過的街之間,車來,車往。這永遠轉動著的無名世界。寶寶和我在原地一動不動,彷彿她明白,有個選擇非做不可。
非做不可嗎?重大的事才是偶然發生,別的都是計畫好的。
我繞著那個街區走,想說再考慮考慮吧,只是兩條腿卻往家移動,有時候,你的心最清楚該怎麼做,你只能接受。
進了家門,兒子在看電視。昨晚暴風雨的最新動態,外加某人某事。幾張政府官員老面孔,講老掉牙的那套話,接著又播出了呼籲目擊者提供線索的訊息。那個死掉的男人,名叫安東尼.剛薩里斯,墨西哥裔。死時身上帶著護照。謀財、害命,在這城市算不上希奇,希奇的是天氣變成這樣。 不過還是有件希奇事。他丟下了寶寶。
「你哪知道,爸。」
「我心裡有數。」 「
我們應該報警啦。」
我怎麼會養出個相信警察的兒子?我兒子不管誰都相信,實在讓我擔心。我不禁搖搖頭。他手一指,指向寶寶。
「不報警的話,那你要拿她怎麼辦?」 「
養她啊。」
我兒子滿臉驚愕,難以置信。我沒法養一個剛出生的寶寶,再說這也是違法的,可是我豁出去了。「幫助無助之人」。我就不能是伸出援手的人嗎?
我已經餵過她,也幫她換了尿布。從醫院回家的路上,我把該買的東西都買齊了。倘若我太太在世,也會做同樣的事。我們會同心協力。
這感覺就像──我奪走了一條命,所以現在有人把一條命交給我。這對我而言,就像寬恕。
這孩子身邊擺著一只手提箱──活像先幫她預備了從商之路。箱子上了鎖。我對兒子說,假如我們找得到她爸媽,自然會全力去找,於是我們打開箱子。
克羅那表情,完全是低成本喜劇的爛演員──雙眼暴凸,下巴掉到地上。
「七天創造世界!」克羅驚呼。「這玩意兒是真的嗎?」
箱內是一疊疊整齊紮妥的簇新鈔票,和警匪片裡的道具一個樣。五十捆。一捆就是一萬元。
鈔票下放著一只柔軟的絨布袋,裡面是條鑽石項鍊。不是什麼便宜小碎鑽──非常大顆,非常慷慨,如同女人的心。時間在各個刻面中,如此深邃,如此清晰,恍如望進水晶球。
鑽石項鍊下有一份樂譜。手寫的。曲名是〈珀笛塔〉。
嗯,這就是她的名字。這小小的棄兒。
「萬一你沒去坐牢,」克羅下了結論:「可就發了。」
「她是我們的,克羅。她現在是你妹,我是她爸。」
「那你要拿這筆錢怎麼辦?」
我們搬到沒人認識我們的新地方。我把原來那間公寓賣了,用所得的房款和手提箱裡的錢,買了一間叫「羊毛」的鋼琴酒吧。這酒吧原本的老闆是黑手黨,他們得脫手,所以對我用現金付款完全沒意見,一個字也沒問。我把鑽石項鍊用她的名義放到銀行保險箱,寄放至她十八歲。
我照樂譜彈那首歌給她聽,教她唱。她話都還不會講,唱歌倒先會了。
我學著當她的父親與母親。後來她問起生母,我說我們一無所知。我對她總是說實話──或者說,她該知道的實情我自然會說。何況她是白人,我們父子倆是黑人,她當然知道自己是撿來的。
故事總得有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