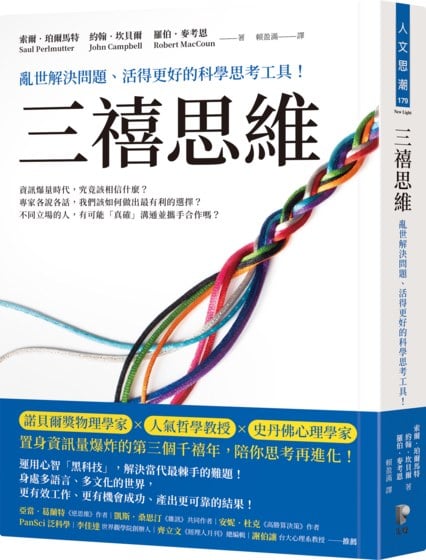在充滿不確定性和兩極化拉鋸的世界,由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和法律心理學家合力揭示,如何運用科學工具,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聰明的判斷和更明智的決策。這原本是三位傑出教授開給大學部的一門課,由於從學生的改變受到鼓舞,再發展成為這本被亞當.格蘭特所大力推薦的《三禧思維》。
我們進入第三個千禧年。面對的險勢包括資訊氾濫、心理陷阱、AI崛起、不知所措......,我們最可怕的舊思維是什麼?可以用什麼新思維反擊它?
樊登說書一個月內兩度推薦:好嚇人!
樊登最近兩度提到《三禧思維》,不僅專題說書,又再列為世界閱讀日他第12次年度演講知識進化。他認為:
讀《三禧思維》最大的收穫,是人們很難從「經驗」中學到正確的東西,因為經驗中「雜訊」太多。所以需要批判性思維和科學的方法,去除雜訊,形成真正有效的理論。同樣是方法,根據經驗來的要打問號,根據最基本的原理來的更可信一些。
這本書講的,就是批判性思考的重要。如果想提升自己的思考品質,希望大家都能來讀這本書,而且很棒的一點是,作者說,第三個千禧年(2001~3000)才剛剛過去了百分之二,我們依然大有可為!
機率思考讓你的心智上有足夠彈性
只要思考自己對實在知道多少,立刻就會明白兩件事:我們有很多事不知道,還有很多事仍然不確定。不確定會令人焦慮。身為人類,我們生理上有求生本能:如果不曉得森林裡藏著什麼,進去時最好小心一點。不過,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或只部分知道什麼,其實對生存也很重要,更影響了我們是否能活得好。這就讓我們來到科學思維裡或許是最根本的一種思考模式,也是「三禧思維」的關鍵:有效運用不確定性,讓我們對行動更有信心。
面對這個我們「只知道部分而非全部」的實在,科學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思考角度,讓我們的想法從只能處理自己百分之百確定的事,變成如果能處理確定程度不同的事,我們其實會更成功。除此之外,在這個可取得的證據往往無法給出百分百答案的世界上,光是明白信心有程度之分,就比堅持追求明確答案還有用得多。
滑雪要不摔跤,你需要的穩定是不斷讓身體重心在兩腿之間移動,也就是所謂的動態平衡。同樣的道理,當我們需要依據對實在的理解做決定時,其實不必要求自己目前所信的一切必須為真,而是相信其中某些事情多一些、某些事情少一些,並隨著自己對世界的新認識而調整,以便必要時修改我們的決定。這是科學最重要、卻也是最少被人提及的絕招,我們稱之為機率思考。這個絕招讓我們心智上有足夠的彈性,得以靈活應對理解世界時的「不確定性」坡道。
許多人仍然堅守不堪一擊的二元觀,認為經驗命題(從新藥效力、飲食計畫到刑事司法政策等等)非對即錯。在他們眼中,只要有一個反例,例如「我舅舅打了疫苗還是得了流感」,就足以讓原始主張完全不值採信。這或許是讓提出主張的科學家如此尷尬的原因之一。
「我可能錯了」,讓你能依然自豪自信
科學家已經擺脫這種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建立了一套可以提出任何帶有暫時性質的主張的文化,而這種暫時性——認定每個命題都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正是科學之所以強大的主因之一。它讓我們不會執著於當下擁有的特定想法,不需要倚靠自己所有想法都是對的來證明自己,從而保有餘裕,即使有時宣稱「我很有把握這個理論切中實際狀況」,結果錯了,依然可以當個自豪自信的科學家。
科學家學會了幾個表達不確定的好習慣。首先是盡量用數字來量化自己的預測。這個數字就是機率。
就算科學家想表達自己對某件事為真超級有信心,認為它絕對肯定顯然為真,也會因所受的訓練而難以說出「對,百分之百,這件事絕對肯定顯然為真」,而是可能說他們有99%,甚至99.9999%的信心水準說自己對某件事有99.9999%的信心水準,基本上等於說「我願意拿生命擔保這件事為真」,但也表示「我知道自己還是有可能錯」。
能放下絕對肯定句,是擁有「機率思考」這項超能力的首要關鍵。
假如你懂機率思考,就更可能認真考慮這樣的假定反事實:「嗯,好吧,我很確定是這樣沒錯。我可能百分之九十確定。但要是我搞錯了,那會怎樣?」當情況是遛狗,這個問題可能不是太重要,但換作其他情況卻可能帶來(也真的帶來過)有趣的科學結果。因此,將「假定反事實」當成「其他情況」,並認真考慮這些情況確實反映實在的機率,就成為很有用的做法。
練習:說說你對自己的發言有多少信心?
有個練習,不僅可以讓你體會每回提出主張或在圖上標一個點時,能量化自己的信心強度有多重要,還能將這個方法融入到你做的幾乎每一件事裡。
我們希望你能根據自己對發言內容真實性的信心水準,來一場真正的對話。你可以挑選任何主題,只要這個主題有許多不同意見就好。例如,假設你和一群朋友正在討論,幼稚園到中學增加標準化測驗的比例是讓教學品質變好,還是變壞。
討論過程中,只要有人提出有真假可言的主張,就要立刻補上0到100之間的一個數字,代表他們目前對這個主張為真的信心強度。萬一有人忘記這樣做,其餘夥伴就要打斷他,要他補上信心值才能往下說。有時停下來討論你不是那麼有信心的事也很有意思。
譬如你對自己剛才那句話的信心水準遠低於95%,這時就可以問自己:「萬一我是錯的,最可能出錯的地方在哪裡?而我該問什麼問題,才能對我不知道的事情知道更多?」
一旦找到可以忍受這樣討論事情的朋友,你們或許會察覺有趣的事發生了,而且和主題一點關係也沒有。嘗試過這種方法的學生表示,每當發言者給自己的話很高的信心強度,就更有壓力提出證據。此外,每當我們聽到別人給出的信心值後,往往也會修改我們自己的信心值。
這些發現點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要是我們社會的人都這樣討論事情,會不會改變討論的進行?會不會讓參與者更懂得聆聽他人?對自己的發言更謹慎?更願意考慮其他情況?或許接下來兩天吃晚餐的時候,你應該強迫同桌的人一起進行這種討論,看看會發生什麼。要是你覺得這樣做會沒有人跟你吃晚餐,或許試個兩輪就好,看看討論氣氛會不會和以前不一樣,尤其辯論主題很有趣的時候。
--本文摘錄整理自《三禧思維:亂世解決問題、活得更好的科學思考工具!》,全文詳見本書第四章
★諾貝爾獎物理學家X史丹佛心理學家X人氣哲學教授
置身資訊量爆炸的第三個千禧年,陪你思考再進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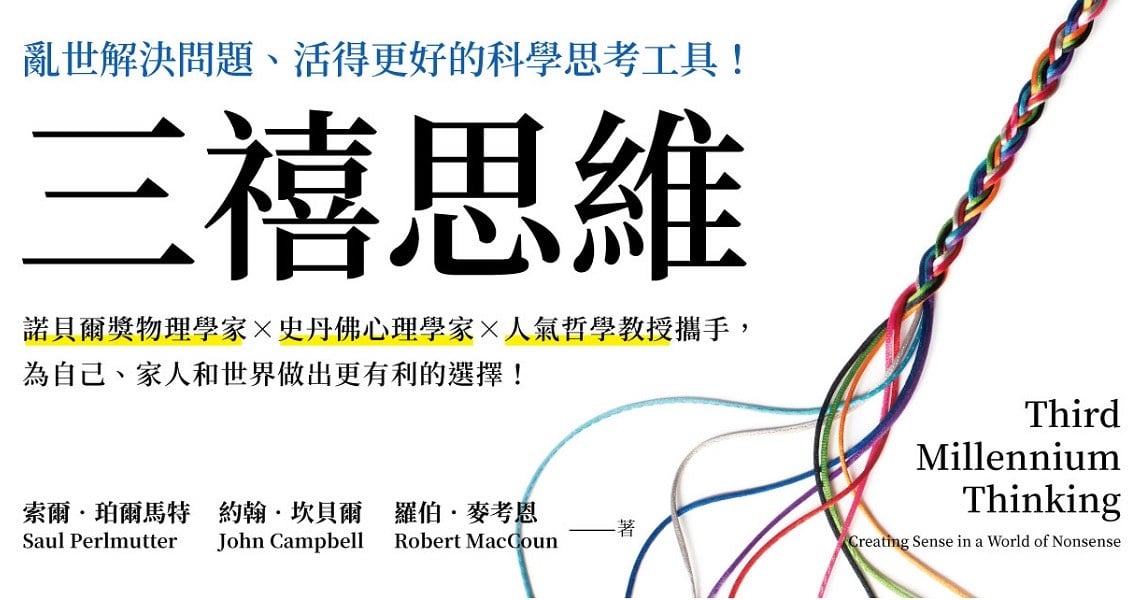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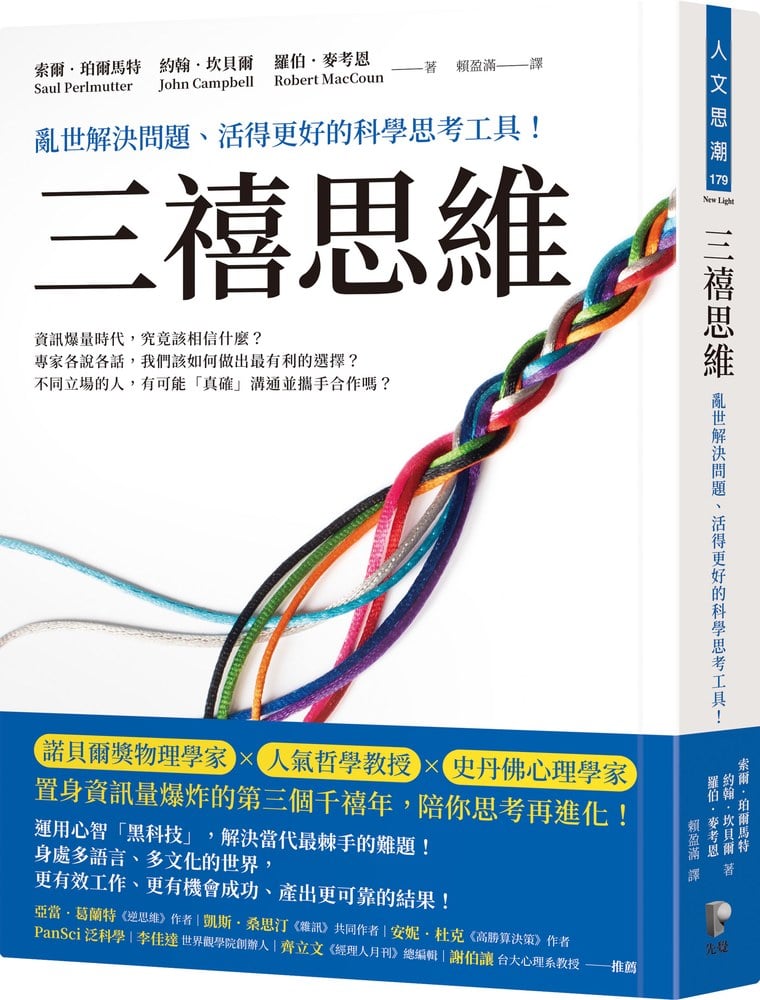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