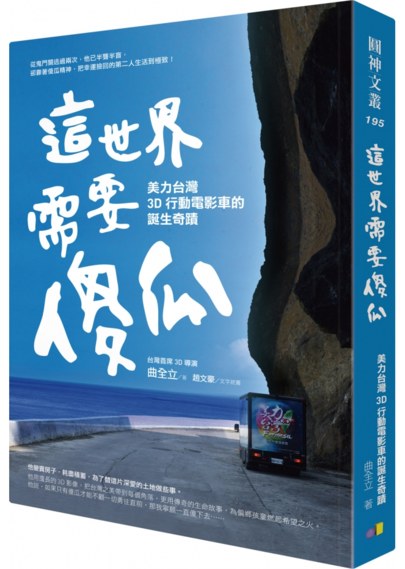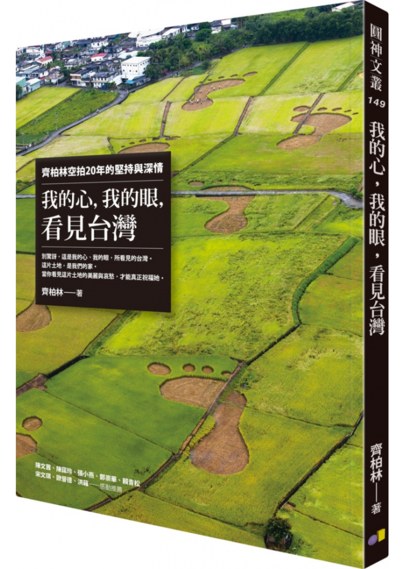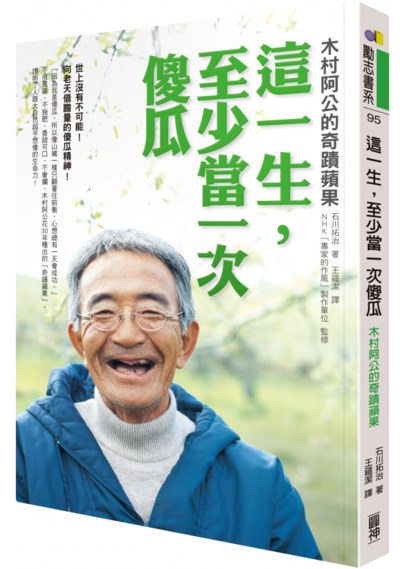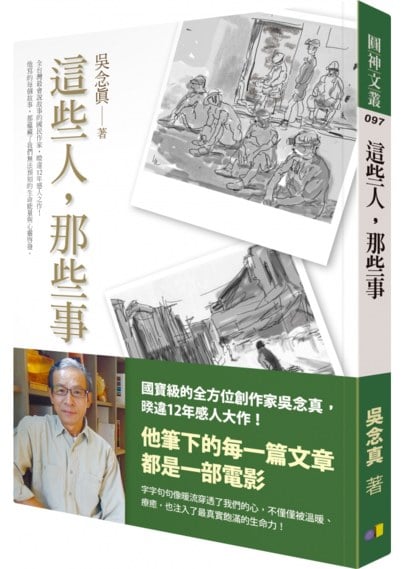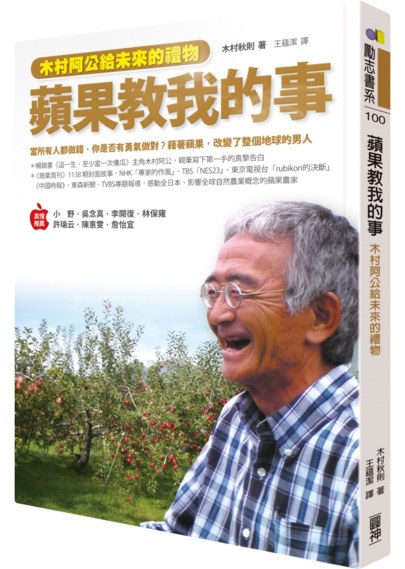那一年,國際I3DS大獎頒給了兩個台灣導演。一個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導演李安,一個是《3D台灣》導演曲全立,當時媒體報導就是一陣台灣之光,忘了繼續認識這位「半聾半盲」的導演。
因為,在台灣知曉曲全立的有兩種人,一種是傑出的業界人士,侯孝賢、徐克、五月天……;一種是我們不認識的台灣美力,例如被孩子稱為「爸爸」的校長,安排插隊修車、只收工本費的修車廠老闆,以及志願是當3D車司機跑透透的小二生。
出生時由於父親已經罹患漸凍人症狀,擔心被遺傳的曲全立,在家人的討論與投票之下,以一票保留小命。跟所有男孩一樣健康調皮的曲全立,畢業後面對茫茫人生時,看到徵求攝影助理的廣告,可以從租處騎腳踏車就到工作地點了,在省車資很高興的前提下進入影視圈,卻沒想到十數年之後,卻為台灣創造出KTV近萬支伴唱帶,以35mm拍攝音樂錄影帶的規格,驚豔四座。
他在35歲達到事業高峰時,感覺身體不適前往就醫,雖然不是罹患肌肉萎縮,卻是發現一顆壓迫了六條神經的腦瘤。從來沒有與父親合照過的曲全立,先是安排一系列與小孩、妻子的合影,再剃個大光頭,進行28個小時的手術。醒過來之後,單耳失聰,單眼失明,還有一些臉部麻痺症狀,但他還是深感「知足」,可以參加女兒的幼稚園畢業典禮,工作效率風風火火,嗓門依然很大,但是多了「情」味。
而且…..正式成為「頭殼壞去」的傻瓜。

有人說曲導跑太快了。他說:那是因為我必須把握每一分鐘。
美力台灣開跑前的重重挫折
頭殼壞去是稱讚
其實我一直覺得,「頭殼壞去」對我是一種稱讚,因為那代表著不計個人的利弊得失,勇往直前。
當美力台灣這個想法成形之後,我興奮地告訴身邊的朋友,想跟他們分享這個好點子。但他們的反應就像我剛開始要投入3D電影時一樣,紛紛勸我打退堂鼓。他們說,這樣的事情吃力不討好,要先花一大筆錢不說,即使真的做了,在現今的社會氛圍下,又有誰會因為這樣的事感動?這麼做改變不了什麼的。
雖然知道他們的關懷出於真心,而且擔憂我在動過重大腦部手術以後,是不是還有能力禁得起未知的後果或挫折?但我聽在耳裡多少還是有點難過的。不過,我對這塊土地與土地上的人們都有信心,我相信這樣的事一定會對某些人有意義。而究竟是誰?這個答案就需要我們一起去找尋了!做了才知道,不做都是空談。而我,必須率先做起。
於是我畫了一張3D車的設計圖,這是綜合之前製作3D電影的經驗與放映條件的考量。我希望車子裡頭要有3D螢幕、環繞音響,要有比擬電影院設計的遮光效果,還必須要能耐得住跋山涉水的震動。這部車子必須要能從台灣頭跑到台灣尾,即便在鄉間小路、崎嶇陡峭的彎路都要能通過。最重要的是,必須具有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夠播映3D電影的功能。
紙上談兵很容易,真的做了,才發現沒那麼簡單。
在Ted演講中,我曾經提過這個3D行動映演計畫,後來有許多人跑來跟我討論3D拍攝之外,更好奇美力台灣的行動映演計畫。許多公部門與各大基金會的人知道了這個計畫以後,更是紛紛到公司跟我說要支持這個計畫。他們說,經費的缺口他們可以幫忙補足,其他任何需要協助的地方,也都願意一起來努力。
「看起來這次會很順利!」聽著這些承諾,我開始對這個即將開跑的計畫充滿信心,這次看來不會像我之前研究3D那樣碰一鼻子灰了吧!
我開心地拿著3D車的設計圖到車廠詢問怎麼打造這部車,想要討論怎麼讓這些需求成真,沒想到跑了十幾家,每個師傅看到設計圖的反應都一樣──眉頭一皺,然後一口拒絕,還順便熱心地提醒我這種車根本不可能做得出來,不用花時間再問了。
跑了許多知名車廠,碰了許多釘子後,我乾脆回到汐止的一家小車廠,裡頭的黑手臉上與衣服滿是黑色的油垢,一邊嚼著檳榔,一邊伸手跟我要設計圖來看。「你確定真的要做這樣的車嗎?」他大概很難相信有人這麼天馬行空,畫出這種想都沒想過的設計圖。於是轉身去找老闆一起評估,看要不要接下這個案子。

美力台灣3D車,就像一顆善心雷達,吸引無數善良的力量。包括路上幫忙推故障車的阿伯;說服一間間育幼院老人院「這真的不是壞人」的志工媽媽團;指點GPS上不存在的小學的居民。
「做!遇到問題解決就好了嘛!我就是要做一部可以放3D電影給孩子看的車,真的有這麼難嗎?」我開始有點氣急敗壞,因為實在遇到太多人直接拒絕這個構想,連理由也不說,一口拒絕,我甚至不斷透過友人的介紹與打聽,希望找到願意接案的車廠,但還是換來一盆又一盆的冷水。
「這部車要花很多錢喔,而且你的圖這裡要改、那裡要改……最重要的是,以前沒有人做過這樣的車子,所以除了花錢,我們還要花很多的時間。這些時間我們都可以再做五、六部車的生意了。」他們口裡說出的每一個字都像一顆巨石,敲得我的腦袋轟轟作響,看來這個願望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實現。
不過沒關係,至少他沒有拒絕我。
王老闆終於點頭答應接下這個艱難的案子,並請師傅阿賓跟我們一起討論這部車要如何成形,如何做修正。於是我們拿著設計圖,一項一項逐步討論。我知道這部3D車一定所費不貲,但幸好先前有許多人都答應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想到這,我振奮了起來,於是擬了一份簡單的企畫與預算,準備展開打造3D車的計畫。
一塊錢也沒募到
當我寫完企畫,真正開始進行募資的時候,當初信誓旦旦說要協助的公部門與基金會,不是沒有回應,就是他們自己也遇到難題,沒辦法提供協助了。我每天電話一個接著一個地打,但希望也一個又一個地落空。我原先的樂觀早已支撐不住,非常氣餒,看來3D車真的只能胎死腹中了。
在這萬念俱灰的時候,我突然接到車廠師傅阿賓打來的電話:「頭家!你要的車,王老闆已經幫你找到車款了,只要用這台車來改,你要的那些條件我們都可以做出來了!」
這太令人振奮了!原本幾乎不可能做出來的車子已經有了一線曙光。但是,車子就算到位,沒有資金還是不行啊,募不到款項,車子怎麼做得出來?想來想去,沒有別的可能了,於是,為了夢想我只好「再」賣一次房子。
但這次賣的,是我半輩子的心血,是我在內湖的前一個辦公室。

在這一路上,曲導發現,原來最重要、也是他想做的,是「陪伴」。
取是能力,捨是境界
就如前面提到的,我的第一間公司辦公室位在地下室,那裡空氣不好、環境也差,但身上實在沒有多餘的預算,所以就從那裡開始發跡。後來賺了一些錢以後,我帶著團隊與大批器材搬到內湖。雖然地方不大,但在這小小的空間裡,我們拍出讓老外瞠目結舌的3D影片,徐克導演多次祕密來台請益3D技術、侯孝賢導演看到我在3D的成果叫我繼續做下去、五月天3DNA演唱會電影的誕生、台灣第一部3D真人實拍電影小丑魚、許多記者與產業界人士來訪、看著三個女兒,還有公司的孩子長大……
儘管總是被質疑這麼小的空間,我們要如何做好3D拍攝、調光、剪接、以及Show Room?但我們真的做到了!歷經這麼多辛苦以後,我們終於存夠了錢,將公司搬到隔壁棟更寬敞的地方。在這裡,有我太多的故事與回憶,要賣,實在捨不得。
但為了讓「美力台灣」可以走下去,我必須捨去某些東西。
於是我毅然決然地把這個地方賣了,並再跟銀行借貸了一筆費用,這些錢剛好讓我可以製作這部3D車,並讓活動能持續運作一段時間。
其實,當我準備簽字賣房的前幾天,有個基金會打了電話過來,說他們聽到這個3D車的偏鄉映演計畫,很希望可以協助我繼續下去。這個消息當然很讓人高興,但正式坐下來談的時候,對方卻告訴我他們自己有車,所以我只要把3D影片讓給他們就好。我看著他像打開水龍頭一樣劈哩啪啦地自顧說著他們基金會的宗旨,說著3D車可以如何結合他們的計畫,並且輕描淡寫地說讓他們來跑就好,我不須插手,這些話聽在我的耳裡,心痛不已。
尤其是,他們希望我可以無償並且無限期地提供他們使用我所拍攝的3D影片。
拍攝影像的版權原本就非常難去界定,這在我的心裡一直是個痛,而在這次談話中,他們似乎將「影片」看作是一項商品,完全不顧影像工作者所需要的尊重。這個問題一直都在,我在得了3D獎回台以後,也屢屢有這樣的感受。正因為我一直對這樣的現象感到不平,所以更覺得「美力台灣」這樣的計畫值得我用心用力去做。
於是我決定婉拒美其名的援助,賣掉工作室,我要做我想做的事。
--本文摘自《這世界需要傻瓜:美力台灣3D行動車的誕生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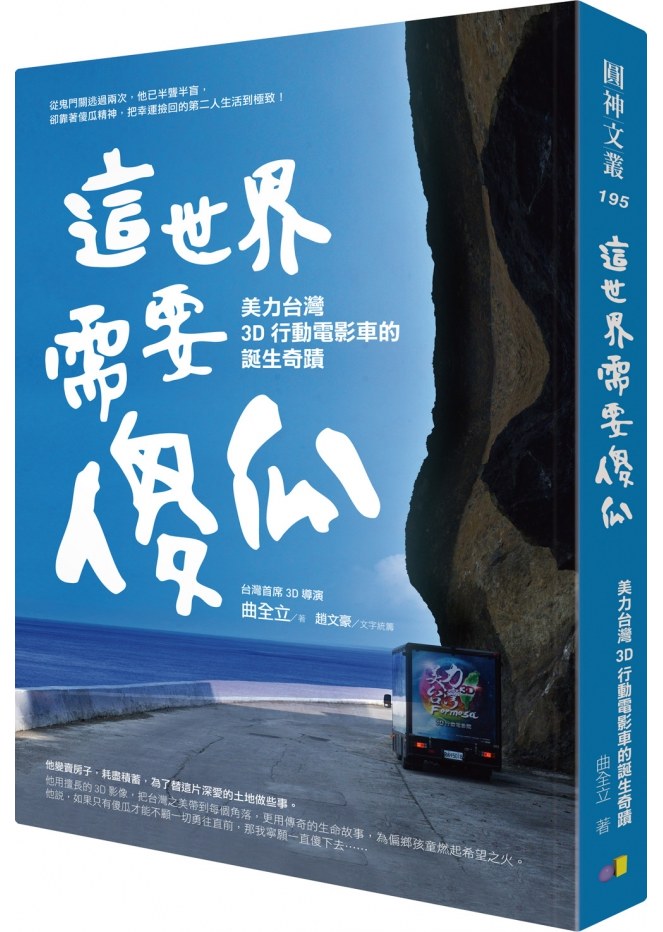



.jpg)
.jpg)
.jpg)

(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