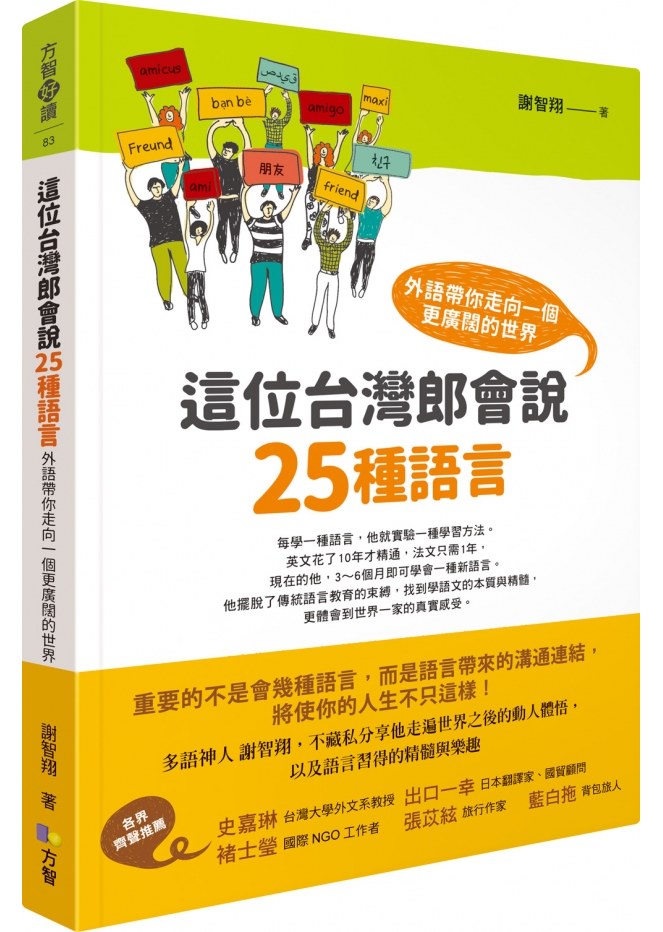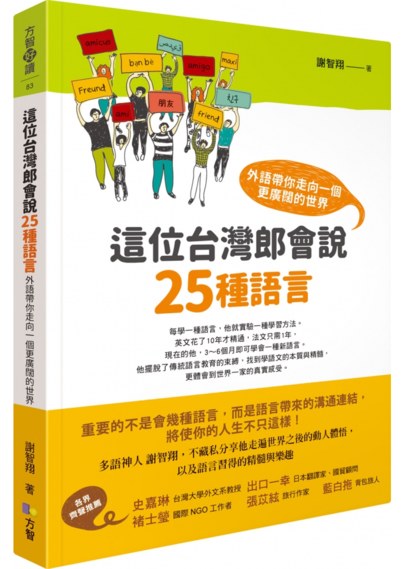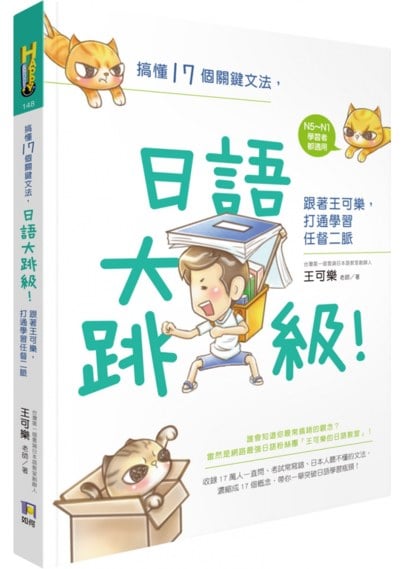(圖為作者Terry在日本打工,賺生活費兼練日文)
會說25種語言,被封為多語神人,連日本媒體也報導過他的謝智翔Terry,每學一種語言,他就實驗一種學習方法。英文花了10年才精通,法文只需1年,現在的他,學會一種新語言,3〜6個月即可做到。
他認為,學習語言的心態很重要。語言是一種習慣,習慣就會了。請給自己多點信心!
出自《這位台灣郎會說25種語言:外語帶你走向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我們都喜歡向成功的人學習,想賺錢就跟有錢人學,想學跆拳道就跟金牌教練學,想學語言就效法語言好的人,很少有人會去跟「失敗」的人學習。
學習各國語言的同時,我也在尋找「學語言的袐密」,嘗試解開多年來的各種疑惑。我拜訪了所謂「語言教育成功」的國家如荷蘭和瑞典,卻看不出端倪,多年下來踏破鐵鞋不得梅花撲鼻香。就在山窮水盡之時,我在一個看似緣木求魚的地方找到了答案。
這個國家的語言教育常被世界各國揶揄,甚至被稱為語言教育最失敗的國家,也許正是因為太失敗,才能醞釀出這麼深厚的語言思想。
我在日本,發現了學語言的聖杯。
◎日本甲子園的打工度假生活
退伍後,我前往日本大阪打工度假半年。在法國留學時有一群日本好友,我們都用日語交談,一整年相處下來,我對日語建立了很強大的信心,認為自己既然可以跟日本人自然地交談,到日本之後應該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然而,當我開始找工作,信心指數就不斷下滑。因為不知該從何處找起,我先撥了通電話給全球知名連鎖速食店詢問打工機會,雖然電話面試一切順利,沒有溝通不良的情況,但還是被發了「謝謝再聯絡」卡。之後,我大概打了五十多通電話找打工機會,有三分之二在電話裡就被拒絕了,剩下三分之一的雇主雖然願意給我面試機會,但面試之後也都沒有下文,只有一間小旅館的老闆跟我詳細說明了理由。
他覺得我日語不錯,但還是想找日語能力接近日本人的外國人;對他來說,「普通流利」跟「不太會」的人並無太大的差別。他建議我再多試試,真的缺人的時候,少部分雇主會願意給外國人機會,那時對他們來說,語言程度就沒有那麼重要。在此給準備去日本打工度假的朋友一個建議,找不到工作不要氣餒,那不一定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也跟日文程度不一定有關係,只要繼續找就好,總會碰到願意用外國人的雇主。
國際上的交流和在另外一個國家工作、生活,是很不一樣的事,周圍的人對你也會有不同的期待,如果說留遊學是教你在國外生活,那打工度假就是教你在國外生存。從「日語很不錯」變成「有待加強」的確很不是滋味,但也只能放下過去,調整心態,重新學習。
除了找工作之外,我每天都會定時閱讀日本的報紙,參加各種可以跟日本人交流的活動,兩個月後,雖然我不覺得有什麼實質的進步,但很幸運地找到了三個有趣的工作,正式開始了在日本的打工度假生活。
其中的兩份工作都跟收銀有關。一是在便利商店—這份工作只要把錢算正確即可,並不複雜;二是在甲子園球場—我必須記下客人點了什麼餐點,非常講究對語言的反應與敏感度。甲子園球場是日本最大的棒球場,每次比賽時的觀賽人潮非常多,販賣飲食的攤位總是大排長龍,收銀員必須同時收錢,同時記下客人點的餐點,之後馬上要接待下一個客人。我當時做得非常辛苦,無法又收錢、又跟上各種客人點菜的節奏,這件事讓主管一個頭兩個大,後來只好盡量安排我去做非收銀的工作。
這個經驗讓我體認到,學語言其實有兩難,一個是了解語言背後的文化意涵,例如看懂美國總統選舉的辯論;另一個是在分秒必爭的情況下使用語言,例如在爆滿的麥當勞收銀。或許只有達到這兩個境界,一個「fob」才有辦法進化成「fobulous」—一個學好道地美語又深諳美國文化的亞洲移民。
在便利商店和甲子園球場工作半年後,我雖然離「fobulous」的境界還有一段距離,但已習慣了收銀工作,不會像一開始一樣手足無措。我不覺得學語言一定要以成為母語人士為目標,但語言學習確實沒有盡頭,應該要持續地力求進步;不必強迫自己一定要達到某個程度,只要可以很舒服地使用一種語言,我們就算是「會」了,也可以算是「精通」,確實掌握了語言;如果因為外在情況改變,我們不再感到輕鬆或是自在的時候,就該努力精進。
回到「會一種語言」這個問題,我想最好的答案就是:語言是一種習慣,習慣就會了。請給自己多點信心,只要對一種語言感到舒服自在,我們就已經掌握了語言。
我會說日語,因為日語讓我感覺很舒服。

(圖為作者Terry在大阪青年旅館工作的夥伴)
◎311 大地震,危難中體認到世界一家
大學時,高志綱在亞錦賽對韓國打了再見安打的那一刻,是台灣棒球運動近年來的最高峰,也是抗韓、反韓情緒的最高點。我也跟隨著潮流,加入了「韓國人都作弊」的行列,這種莫名反韓的情緒在日本度假打工時起了變化。
除了甲子園球場和便利商店,當時我最主要的工作是管理背包客棧,要打掃也要接待客人。這間位在大阪難波的背包客棧,與一般人對背包客棧很「國際化」的想像不同,沒有太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八成以上都來自韓國,十成的日子也不少。因此,我不得不對抗心理上的不情願,開始學韓語並大量接觸韓國人。
不得不說,仇恨、歧視、迷戀或是崇拜,其實都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我在巴黎時,並不覺得法國人比較浪漫,法國人自己也覺得這個評語匪夷所思;韓國人當然也不是都愛作弊或是都去整形。
在背包客棧工作的那半年,我跟形形色色的韓國人喝酒、逛街、煮飯、划拳,幾個月下來,我發現他們跟我沒有什麼不同,我們都是因緣際會出現在這家旅店的過客,大家都喜歡旅行,也喜歡來日本玩,因此我漸漸放下了反韓情緒。
身在日本卻每天跟韓國人在一起的日子持續沒多久,一場突如其來的事故,改變了這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韓國人聚集現象。
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前後,我在走回背包客棧的路上,地面突然劇烈搖動,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我也來自有地震的國家,所以對這場稍大的地震並不以為意,但一回到客棧,老闆就很大聲地宣告:「在這邊都搖這麼大、這麼久,某處一定有很大的地震!」我們打開電視,NHK 正播放海嘯侵入日本東北沿海地區的畫面,在大阪的我們終於了解了事情的嚴重性。
沒過幾天,福島核電廠的新聞報導出來,一位叫「枝野」的長官每天都會向全世界報告核電廠情形。我們邊看電視,邊接取消預約的電話接到手軟,正想說一整年都不用做生意的時候,來自日本國內的預約電話突然如洪水般湧入,背包客棧的床位很快又滿了。原來,核電廠的新聞出來後,一些住在東京和東北的日本人相繼離開,往西邊避難了。
第一組來避難的客人來自關東茨城縣有名的納豆產地水戶,水戶離福島核電廠只有幾百公尺,狀態不明時他們第一時間就離開了家鄉,往西邊逃難。之後,陸陸續續來了各種平常不會出現在旅店的人物,像是英文老師、美國籍的前相撲選手、被爸媽強制要求回家的台灣人等。這時會說各國語言的我,終於可以說韓文之外的語言,舒適感稍微消弭了地震帶給我的陰霾。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群來自筑波大學的學者。這群學者都是來自世界各國的菁英,他們在筑波大學從事各種尖端研究,像是機器人、高能物理和粒子物理。其中一對俄國夫婦是核子物理學家,先生更是在車諾比附近長大,對核災有相當深刻的認識。他每天都會很細心地研究各種數據,告訴我們各種可能的情況,安撫我們不必驚慌,如果真的整個日本都有危險,他會第一時間告訴我們。
雖然是尖端科學者,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馬上冷靜下來,依數據判斷情勢。研究機器人的法國人一刻都不想待在日本,到我們客棧的隔天,馬上就飛往韓國再轉機回法國;德國人在駐日德國大使館宣布要撤離所有人員之後,不管機票多貴也馬上離日。
當時還有很多很混亂的情況,比如說大家搶著買碘鹽和其他不明的「抗放射線產品」;網路上各派人馬奮力筆戰,用鍵盤決定日本的未來。即使如此,大多數的人選擇在我們的旅店住下,等情況明朗後再決定,畢竟誰也不想放棄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和穩定的生活。不過,到了四月底,幾乎所有人都決定要暫時離開日本,我們的背包客棧也就開始每天大唱空城計。
人去樓空,我想念起這三個多月來遇到的各國人物,想著我們之間到底有沒有真的不同,人跟人之間到底有沒有跨不過的障礙。因為輻射能危機,大家共患難的時候目標一致、同心齊力,感受不到任何語言或是文化的障礙。或許那些文化障礙和語言障礙都是我們閒閒沒事的時候想出來的,歷史仇恨也不是我們的本意,我們該如何跳脫這樣的輪迴呢?我想我們需要靈魂出體再附到別人身上,轉換我們的觀點,用別人的角度來看世界。
看更多:多語神人一年精通法文,還會印加古語,學語言的關鍵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