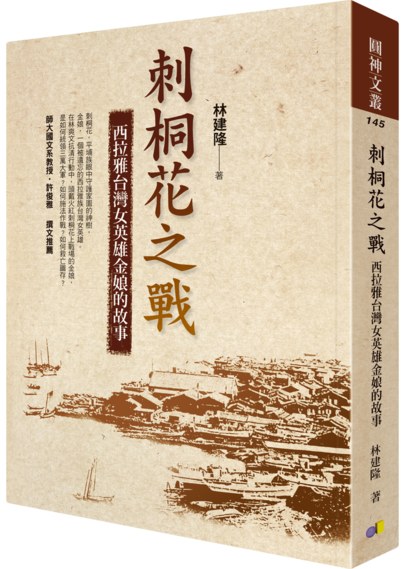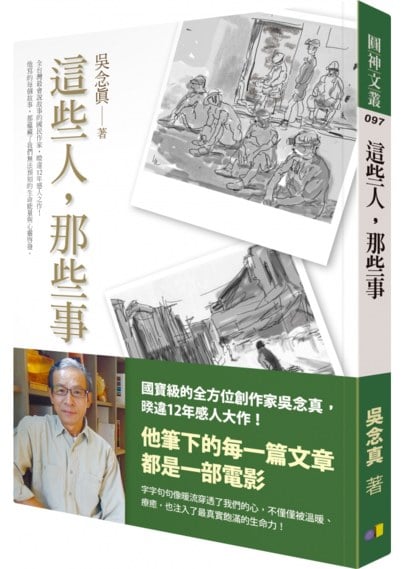◆您睽違文壇多年,為何選擇以《刺桐花之戰:西拉雅台灣女英雄金娘的故事》作為與讀者久別重逢的著作?
金娘是比秋瑾早一百二十年的反清女英雄,但她被後人遺忘了。她是平埔最大族群西拉雅族的大頭目,但她的族群因被迫漢化而滅族/滅祖了。她是西拉雅族阿立祖信仰的大尪姨,但這個最本土的宗教消失了。她的漢人戰友們,如林爽文、王芬、莊大田等,明明是台灣人的民族英雄,也被殖民統治者利用虛偽造假的歷史加以毀容鞭屍。我們的先人為了這塊土地,不惜三年一抗,五年一爭,犧牲青春性命的結果卻只換來敵人利用歷史打造的鐐銬與牢獄。
這些年來我投入台灣人要求轉型正義的運動,但政治結構的牢不可破讓我重新思考回到文學的領域,特別是著眼於小說的大眾性,希望至少能替自己的先人重建歷史的正義,還給他們公道。我相信歷史正義是可以靠文學之筆做局部重建的。我們不能讓「沉冤代雪」成為台灣人歷史的主軸。洪仲丘不能冤死,我們的祖先也是一樣。敵人既已坐在歷史翹翹板的一端,打擊抹黑我們的先人,我就讓我的小說坐上翹翹板的另一端。我的小說重量當然不夠,但只要廣大的台灣子弟和我坐在一起,歷史的翹翹板就能平衡。轉型正義屬於歷史的部份我們也能自己完成。不要讓敵人來寫我們祖先的故事,否則那就是台灣歷史的全部。我們可以自己解開仍加諸於我們祖先手腳上的歷史鐐銬,將他們從歷史的牢獄中釋放出來,不必看執政者的臉色。
◆從師大許俊雅教授的推薦序中聽聞林爽文向您託夢的怪事,能否請問詳細的情形?
過去六年,我有四年忙著在生病,生病期間除了西洋文學的教學,只有足夠的體力閱讀能夠幫助我了解「我是誰」的台灣史書。我悲觀地以為除了教學和勉強讀一些本國史,我是再無體力寫書了。然而就在兩年前的一個冬夜,我忽然夢見林爽文,這個夢讓我悲觀的情緒一掃而盡。他的長相就如同我在《刺桐花之戰》中描述的,三十歲左右,中高身材,十分結實。他臉部的線條有稜有角,一雙劍眉明顯刻劃出性格的剛毅,深邃的眼睛射出的光芒比星星還要明亮。他那堅挺的鼻梁與穩重的人中交會,正面看就像一支閃著靈光的秤子,給人一種平衡公正的信賴感,是典型領導人的面相。夢中他不斷地左右橫移,明亮的星眼似乎一直在搜尋握在我手中的史冊。醒來時記得昨夜是讀到林爽文在北京被乾隆凌遲三千六百刀而死,我一時悲痛莫名抱書痛哭,之後覺得體力不支,一陣暈眩就昏睡過去。但醒來後我竟神奇地感覺神清氣爽,通體舒暢,每一顆細胞都像是新換過的,充滿前所未有的精神與活力。
然而我只高興半天,便開始對自己身體的突然好轉感到懷疑,懷疑這會不會是所謂的「迴光返照」?我開始覺得害怕,從沒想過這樣的身體變化是否和夢見林爽文有關。之後我變得食慾大振,進食都以碗公裝盛。體型雖仍瘦削,卻一點也不羸弱,散起步來變得健步如飛。就這樣過了一個月,「迴光返照」的疑慮解除。我進一步感覺大腦異常的清醒,小腦的反射十分敏銳,閱讀能力更是精進到令自己驚訝的程度。在寒冬即將過去的一個早晨,我又夢見林爽文。這回他是左手捧書,右手翻著書頁,邊翻邊抬頭對著我微笑。我沒來由便認定那是我寫的書,還恭敬地等著聆聽先人的教示。醒來我才不得不相信這是林爽文對我有所託的夢兆。所謂「凡有所託,必有所佑」,我病體突如其來的康復也獲得了合理的解釋。於是當下我便決定為他和他的戰友們,尤其是我最敬佩的西拉雅女英雄金娘,寫一本書,一本後設的,「拒絕讓敵人寫我們祖先的故事」的歷史小說。
寫作初期我因對自己的體力仍不具信心,只打算寫個八、九萬頂多十萬字即止。沒想到提筆跟隨林爽文、金娘和王芬等人征戰的腳步,自己竟也愈戰愈勇起來。我深信即使我全靠想像也比敵人的講法真實,何況我也不全依賴想像。基於這個信念,我放手讓想像天馬行空,儼然是林爽文的文學乩童。說也奇怪,就在我寫完八、九萬字準備做結時,忽然間大量的戰爭場面和我做夢也想不到的情節像連環圖畫般一一浮現我的腦海。我變得欲罷不能,而我的身體竟也毫無疲累的現象,反而更加鬥志昂揚。我把所有的圖像,特別是奇詭的畫面,全部輸入大腦的記憶庫,再日以繼夜按部就班將它們呈現出來,直到寫完十七、八萬字方才作罷。這期間我太太經常邊讀邊發出驚嘆,說我簡直就是搭乘時光機回到林爽文的時代。她甚至懷疑我是林爽文的戰友來轉世,否則不可能將二百多年前的戰場時空甚至秘辛描寫得歷歷在目,彷彿身歷其境。
我完書之後,病體也告完全康復。我過去本就相信創作者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乩童的角色,如今有了這番被林爽文選為文學乩童的體驗,更加對此深信不疑。
Q:台灣文學取材於重要歷史事件的長篇小說和戲劇好像特別少,為什麼?台灣歷史上有很多像《刺桐花之戰》的感人故事,為什麼市場上還是中國歷史劇當道?
我這樣比喻好了,莎士比亞的時代現代英文寫作的歷史並不長,英國可供取材的的歷史事件也不多,因此他寫的大部份是歐洲大陸的故事。緊管如此他最受歡迎的作品還是取材自英格蘭的《李爾王》和以蘇格蘭為背景的《馬克白》。台灣在逐漸沖刷掉大中國獨裁專制的歷史教育後,市場回歸本土,擁抱台灣價值是必然的趨勢。我過去寫《流氓教授》,寫幾十年前的純本土故事,就獲得極高的閱讀率,拍成電視劇更獲得超高收視率。我這次寫《刺桐花之戰》,也是純本土故事,而且比《流氓教授》還要精采感人,只是把時間往前推進一、二百年。
雖說長期的政治洗腦造成台灣人對自己歷史認識的貧乏,但一本替自己先人平反的小說,一個揭穿殖民統治者虛假面具的故事,只要以台灣子弟的真心,誠意地加以閱讀,其實不需具備多少歷史知識。對讀者來說確實是如此。但對作者而言,要撥開敵人設下的虛偽歷史的重重迷霧,簡直比寫作本身還難,更別說是創作出能和讀者心心相印的作品了。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台灣作家才有更高的難度可以挑戰。對文字藝術家來說,這何嘗不是一種幸福。
Q:請問《刺桐花之戰》的情節有沒有取自您個人經歷的部分?古今東西的小說家或劇作家似乎不太敢著墨於廝殺的場面,您卻仔細地加以描寫,有沒有反應出您的個人經歷?
有!這部分是我個人的強項,我怎麼可能放過?我年輕時在基隆田寮港混角頭,那時還不時興用槍,打鬥廝殺都用傳統武器,特別是日式的武士刀。我渾身上下從頭到手腳都曾受過傷,右大腿更曾遭到重創。我被以殺人未遂判刑五年,外加一期(約三年)的流氓管訓,就是被好幾把武士刀圍攻,但在我三弟的突圍掩護下,反而將對手殺成重傷。我常說只要能記取刻骨的教訓並善用痛苦的經驗,那麼人生便沒有一條路是白走的。的確,後來我在管訓隊考上大學,從此展開我的文學生涯。我發現即使是擅長歷史劇的莎士比亞和以三國演義聞名的羅貫中,可能因受限於文人出身,對於戰爭廝殺的場面也多以籠統抽象的描寫,如雙方「展開一場激烈的廝殺」或「大戰數十回合」閃避式地帶過。我寫《刺桐花之戰》,尤其是台灣戰神王芬與敵人交戰搏鬥的場面,確實是仔細回顧了自己不堪回首的經歷並運用過往豐富的見聞。像這樣具體而微,歷歷如畫的描寫,我自己還算滿意,希望能彌補文學中的武場只能由不具打鬥經驗的文人來書寫的缺憾。
Q:金娘和林爽文是《刺桐花之戰》的男女主角,除了他們以外,你最喜歡的人物是誰?
王芬!我喜歡王芬絕非個人的偏好,而是反應台灣人只要聽過王芬就會喜歡這位台灣真英雄的共同心理。他和三國演義裡的關公有諸多神似之處。他身形十分偉岸,「站著就像東西塔,躺著就像洛陽橋。」他是鹿港八郊(八商會)的武術總教頭,使一把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關刀。他與林爽文一起復興天地會、號召反清之前,早已是沙鹿、大肚山和鹿港一帶的剿匪大英雄。他雖非天地會五房任何一房的正統頭人,但在滿清的奏摺資料中一直是與林爽文齊名,可見他在當時的台灣人和敵對的滿清心目中的份量。
他渾身散發的凜然正氣與戰神的形象,據說令乾隆不得不在他死後為平息台灣人的眾怒,謊稱是臣下誤解他招撫的美意,派數百人(有說是數千人)以不光明的手段將他圍殺。他死後台灣人不避清廷之諱陸續在沙鹿、彰化、鹿港為他起廟。台灣有句俗語說:「死後去做神」,但到目前為止也只有王芬是死後被正式神格化的本土人物。其他像關公、媽祖、鄭成功、耶穌、釋迦摩尼等均非台灣土生土長。或許有人會覺得奇怪為何不是林爽文被神格化,而是王芬呢?我想這就像是問為何不是劉備而是關公被神格化是一樣的。關公的特殊魅力只有讀過三國演義才能真正體會,王芬也是一樣,不讀《刺桐花之戰》,我再多說也是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