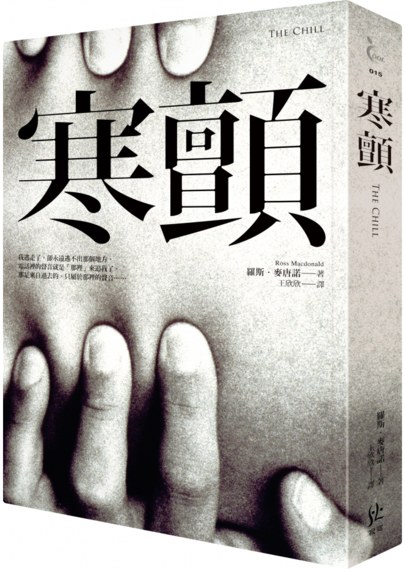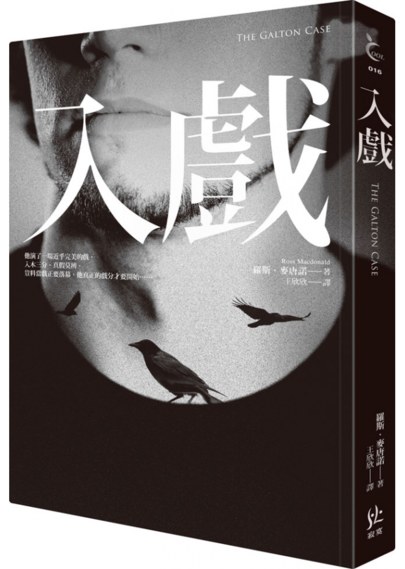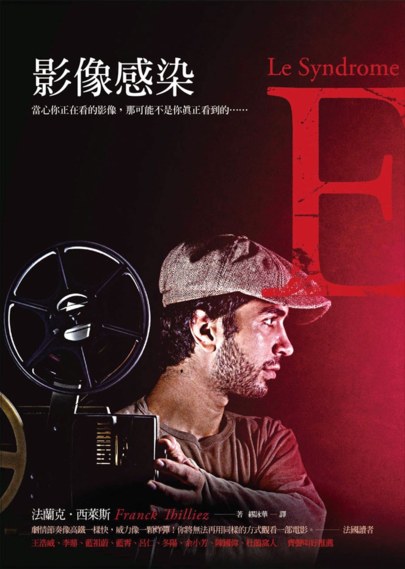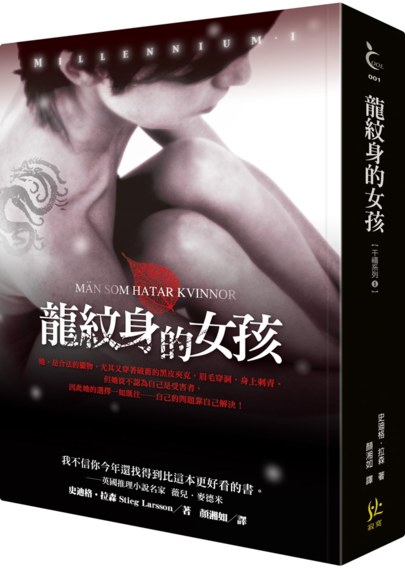月亮已經升起,掛在樹後。我讓思緒隨月亮一起往上升,想像艾力克斯和他的新娘已經重聚,正在小屋裡彼此依偎,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那女孩的哭聲擦掉了我腦海中充滿希望的影像,哭聲又大又慘,止都止不住,簡直不像人聲,而像貓兒受傷發出的哀鳴。
小屋的門沒關好,光從門邊漏出來,就像是被裡面吵雜的聲音擠出來的。我推開門。
「出去。」艾力克斯說。
他們坐在小客廳裡的沙發床上,他摟著她,她似乎在抗拒,想掙脫他的擁抱。他不像抱著妻子,倒像是精神科的護士不想給病人穿帆布束衣,只好用力抱住病人,這種狀況有時得抱上好幾個小時。
她的上衣扯破了,有一邊乳房近乎全裸,頭髮亂七八糟。她轉過頭來,面如死灰,見到我大喊一聲:「出去!」
我對他倆說:「我想我還是留下來比較好。」
我關上門,走過去。哭聲的節奏慢了下來,那其實不能算哭,她的眼睛是乾的,僵硬呆滯,嵌在灰色的皮膚裡。她把臉埋到丈夫身上。
他的臉白得發亮。
「艾力克斯,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太清楚,我在這裡等,她幾分鐘前剛回來,為某件事情難過得不得了,但我不知道是怎麼了。」
「她受了驚嚇。」我心想,他也差不多。「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
「之類的吧。」
他的尾音說得不清不楚,眼睛有點失焦。
「她有沒有受傷?」
「我想應該沒有,她一路跑回來,剛剛又想跑走,我好不容易才制止了她。」
桃莉像要證明自己是個英勇戰士似的,雙手掙脫束縛,朝他胸口打去。她手上有血,在他前襟留下了幾抹紅。
「放開我。」她求他。「我想死,我該死。」
「艾力克斯,她在流血。」
他搖搖頭說:「血是別人的,她的朋友被人殺死了。」
「都是我的錯。」她說話的聲音很平板。
他抓住她手腕,臉上露出了男子氣概。「安靜,桃莉,妳在胡言亂語。」
「是嗎?她躺在血裡,是我害的。」
「她在說誰?」我問艾力克斯。
「某個叫海倫的,我沒聽過那個人。」
我聽過。
那女孩開始說話,聲音很小又很平,講得很快很不精確,我幾乎跟不上。她說她是魔鬼,她爸也是,海倫的爸爸也是。謀殺案使得她倆情同姊妹,她卻背叛了姊姊,害死了她。
「妳對海倫做了什麼?」
「我應該離她遠一點,都是因為我靠近,他們才會死的。」
「哪有這種事,」艾力克斯說,「妳從沒傷害過任何人。」
「你了解我多少?」
「夠多了,我愛妳啊。」
「不要說這種話,這種話只會讓我想自殺。」她直挺挺坐在他懷抱中,看著自己沾滿了血的雙手,又乾嚎了幾聲。「我是罪人。」
艾力克斯抬頭看我,那雙眼睛藍得發黑。「你能理解這是怎麼回事嗎?」
「不太行。」
「你該不會真認為她殺了這個叫海倫的吧?」我們當著桃莉的面討論起來,儼然當她是聾子或瘋子,而她似乎也能接受。
「到底是不是真有人死都還不知道。你太太背負了某種罪惡感,但犯罪的人不見得是她。」我也在床上坐下,對桃莉說:「妳父親叫什麼名字?」
她好像沒有聽見。
「湯瑪斯.麥基?」
她突然點頭,像有人在後面推她。「他是個說謊的怪物,把我也變成了怪物。」
「他怎麼把妳變成怪物的?」
這問題引發了另一串句子。「他開槍射她,讓她躺在血裡。我告訴愛麗絲阿姨,警察和法院就把他抓走了,可是現在他又做這種事情。」
「對海倫?」
「對,而且是我的錯,都是我害的。」
怪了,桃莉似乎很喜歡把罪攬到自己身上。她臉色發青,眼睛流不出淚,說話急得上氣不接下氣,在在顯示情緒快要崩潰。她這樣不斷自責,讓我有種感覺,好像某種珍貴脆弱的東西即將永久毀損。
「最好別再問她問題了,」我說,「她現在可能連真假都分不清。」
「分不清?」她惡狠狠地說。「我記得的事通通都是真的,而且從一歲到現在的事我通通記得,吵架、打人,還有最後他開槍殺她⋯⋯」
我打斷她。「閉嘴,桃莉,否則說點別的也好。妳需要醫生,妳在這裡有沒有醫生?」
「不,我不需要醫生。打電話報警,我要自白。」
我心想,這可不妙,在懸崖邊上表演危險動作,一不小心弄假成真,可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啊。
「妳想跟警方說妳是個惡魔?」我問。
沒用。她不帶情緒地說:「我是惡魔。」
※※※
「我想借用電話,住門房的那位小姐是我朋友。她需要醫生。」
「她生病了?」
「病得不輕。」
「那你不應該留她一個人。」
「她不是一個人,她丈夫陪著她。」
「可是她還沒結婚。」
「我們別爭這個,妳到底讓不讓我打電話給醫生?」
她勉強讓開,帶我繞過弧形的樓梯,走進滿牆都是書的書房。
「能不能讓我有點隱私?待會兒出去的時候我讓妳搜身。」
她吸吸鼻子,退了出去。我想打去海倫家,可是電話簿裡查不到她的電話號碼,幸好葛德溫醫師的號碼查得到。鈴聲響了好久才有人接,那人說話的聲音很小,又很中性,我聽不出是男是女。
「麻煩請葛德溫醫師聽電話。」
「我就是葛德溫醫師。」他聽起來有點厭倦這個身分。
「我叫盧.亞徹,有個女孩子說她從前是您的病人,她婚前的名字叫做桃莉或桃樂絲.麥基,現在狀況不太好。」
「桃莉?我有十年還是十一年沒見到她了,她怎麼了?」
「您是醫生,我不是,還是請您親自來看她吧。簡單來說,她目前歇斯底里,沒頭沒尾一直講謀殺的事。」
葛德溫醫師死氣沉沉地小聲說話,聽起來像過往幽魂在耳邊低語:「會發生這種事我並不驚訝,她小時候家裡出過殘忍的命案,她被迫面對,受到很大的影響,當時又是在即將初經的年紀,很容易留下陰影。」
我聽不懂醫學用語,決定跳過。「她父親殺了她母親,是這樣嗎?」
「是的。」這兩個字說得像一聲嘆息。「發現屍體的是這可憐的孩子,他們就逼她出庭作證。我們居然容許這麼殘忍的事⋯⋯」他突然打住,改用截然不同的尖銳語氣問:「你從哪裡打來的?」
「羅伊.布萊蕭家,桃莉和她丈夫在門房,這裡的地址是⋯⋯」
「我知道位置。」
※※※
我掛上電話,在布萊蕭的旋轉皮椅上靜靜坐了一會兒,書牆圍繞身邊,盡是屬於過去的氛圍,有種與世隔絕之感。我真想一直坐在這裡,不想起身。
有輛車在車道停下,羅伊.布萊蕭走進大門。
他那張臉孔平靜而沒有表情,像熟睡中的孩子。
「葛德溫醫師我認識。」他說。「她受到了什麼樣的驚嚇?」
「詳情還不是很清楚,我得和你私下談。路上談比較省時間。」
「路上?」
「如果你知道海倫的住處怎麼走,請帶我去,我不確定天這麼黑我能找得著。桃莉說海倫死了,手上還有血跡。我想我們最好過去看看血是哪兒來的。」
他愣了。「好,當然好。她住的地方離這裡不遠,其實走小路幾分鐘就到了,不過晚上可能還是開車比較快。」
我們開他的車去,路上我請他先在門房停一下,我去屋裡看看。桃莉躺在沙發床上,臉對著牆;艾力克斯幫她蓋了毯子,垂手站在床邊。
「葛德溫醫師已經在路上了。」我低聲說。「我回來之前別讓他走,好嗎?」
他點點頭,可是沒看我,他正凝視著內心深處那個在今夜之前從未有過的念頭,別的什麼都看不見了。
※※※
布萊蕭的小轎車有安全帶,出發前他要我繫好。從他家去海倫家的路上,我把桃莉說的話告訴他,至少把我認為他該知道的都告訴他了。
這裡除了我們還有另一輛車,應該要去仔細搜查的,但我被罪惡感壓著,一心只想趕快確認海倫是不是還活著,顧不了那麼多。
從下車處望去,她的房子像樹梢後模糊不清的一抹光,有隻貓頭鷹低飛掠過頭頂,靜得像飄過的一團霧,牠的叫聲像遙遠的霧角,彷彿在嘲笑我們。
我沿車道走到屋前,看見布萊蕭坐在門口台階上,一副快吐的樣子。門開著,門裡的光照出來,把他低著頭的影子投射在石板路上,支離破碎。
「亞徹先生,她死了。」
我朝屋裡看,海倫側著身子躺在門後,地板上有一灘從前額彈孔流出的血,邊緣凝固了,就像泥潭上結了霜。我摸摸她悲傷的臉,屍體已經變冷,我手錶上的時間是九點十七分。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