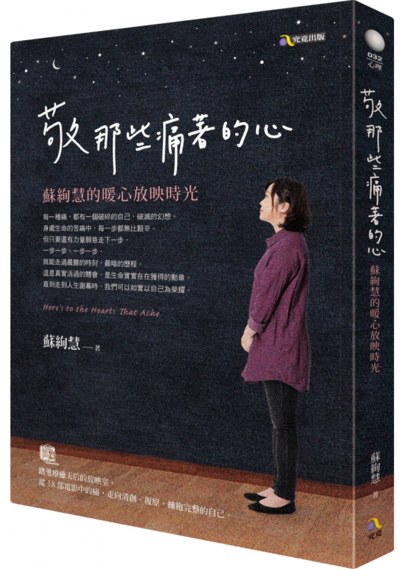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幫普遍不識字的鄰居寫信、讀信已經是我日常的任務。──這些人,那些事【歲月淬鍊增訂版,全新收錄動人篇章】
一般的信,鄰居們通常是拿著信紙、信封直接到我家,交代內容由我代筆;如果事涉隱私,比如對兒子帶回來的女朋友有意見,不希望他們繼續交往,或者跟在外工作的兒子抱怨在家的媳婦不孝、不檢點等等,則是把我叫到他們家或者沒人看到、聽到的地方寫。
阿英從沒跟我講過話,更甭說寫信,所以有一天當她叫住我,說:「阿欽,拜託幫我寫一封信好不好?」的時候,我忽然有點尷尬甚至不知所措。
那時候我已經初中二年級,對男女性事正處於一種啟蒙的混沌階段,而阿英偏偏又是村子裡許多曖昧話題的主要人物,有關她的傳聞甚至早已在我的腦袋裡「畫面化」,所以被叫住的那一剎那,雖然四顧無人,但我不僅聽見自己心臟激烈跳動的聲音,耳邊甚至還響起村子裡所有半大不小的孩子們那種可以想像的詭異的嘩笑聲。
阿英從嫁到村子以來就很少跟人家有交往,原因不知道是她的出身、婚姻,還是某些獨特的行為或打扮。阿英曾經是一個「茶店仔查某」,不知道為什麼卻讓村子裡公認最憨厚、老實的阿將給迷上了,最後甚至不顧家裡所有人的反對,把她娶回家,外帶兩個「父不詳」的孩子。
由於家裡不接受阿英,阿將乾脆在村子尾自己蓋了一間房子,一家四口過自己的日子。
村子裡的女人都嫉妒阿英,因為阿將捨不得讓她出去工作,所以除了帶小孩之外,天天「穿水水、點胭脂、拉機歐(台語:收音機)轉到大大聲,唱歌喇曲過日子」;而阿將為了養太太、養「別人的小孩」,只好天天加班「從死做回來」,不知道村裡的人是不捨還是覺得阿將活該,都說他「日拖夜磨,一年老十歲」。傳聞就從此開始了,說阿將天天拚老命,而阿英卻背著他跟許多賣菜、賣肉、賣雜細的人不清不楚、勾勾搭搭。
一年多前,阿將忽然大量吐血過世了,雖然醫院說死因是多年胃潰瘍所導致的急性胃出血,但許多人還是寧願相信阿將是為了阿英和孩子累死的,甚至還有流言說是阿英每天在飯菜裡摻老鼠藥害死的,說「不信大家看,阿將沒過百日,阿英就會跟客兄落跑!」
沒想到阿英不但沒跑,甚至還開始出門做工養家,而且,也許是不想面對村子裡無所不在的異樣的眼光吧,她選擇到一小時路程外的猴硐去當洗煤工。
那天是我第一次走進那個充滿曖昧傳聞的主場景,但我有點失望的是它跟一般礦工的住家並沒有什麼不一樣,而且收拾得非常清爽乾淨。兩個分別已經小學四年級和五年級的孩子正在寫作業,牆上阿將的遺照彷彿帶笑注視著他們。
「你們兩個先去挑水,把水缸挑滿,我有事要拜託阿欽哥哥……」小孩離開後,阿英跟我說:「有些事……我不想讓小孩知道,所以才拜託你。」
阿英要我寫信去宜蘭老家跟哥哥借錢。
「你要特別寫清楚,說我是跟他借,以後還是會還,不是因為丈夫死了,找理由討人情。」阿英說之前她曾經託人帶過話,可是哥哥回話說,她是找理由跟他討之前她「做事」時陸續寄回家的錢,她有點哽咽地說:「你跟他說,阿將是有保險可以領,但是,我一毛錢都沒分到,連葬禮的白包……也都是阿將的家人拿了了……」
幾天後宜蘭的回信來了。
當她把信遞給我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一雙被洗煤水泡得有點腫脹、龜裂的手,粗粗短短的手指頭上還有一些被石頭或煤炭割傷的疤痕,一如我媽媽的手。
信寫得很直接,她哥哥說沒錢可以借,因為暑假後三個小孩都要註冊,說他自己身體也不太好,得看醫生、吃藥,說他只靠一塊「瘦田」養一家,而阿英在礦山,賺錢的機會至少也比他多……
我看到阿英的臉慢慢垮了下來,當我念完之後,她忽然悶著聲音說:「他的小孩要念書……我的就不用?……礦山好賺錢?他是要我再去給眾人幹嗎?」
我愣在那裡不知所措,不知道該說什麼樣的話,也不知道是該離開或者繼續坐在那兒,尷尬了好一會兒,阿英才拉起衣襟抹了一下臉,抬起頭笑笑地跟我說:「歹勢……這種見笑的事,都讓你知道了……你可不要跟人家講哦!」
那年的中元節之前來了一個超大的颱風,村子裡三分之一以上的房子不是全倒就是半倒。這場災難對礦脈已經衰竭的家鄉來說不啻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很多受災的人乾脆就死心地離開那個曾經繁華一時的地方,於是,颱風過完不久,整個村子就讓人感覺像是在一夜之間蕭條、衰敗下來。
阿英的房子也垮了,村子裡的男人一起去幫她修。父親回來之後,我聽見他跟媽媽說阿英很不會打算,說她大概把阿將的保險金都花光了,說修房子的材料都沒買夠,大家忙了一天,她也只買了一打汽水,連煮個點心什麼的都沒有。
我信守對阿英的承諾,沒跟父親說其實阿將的保險金,根本沒有阿英的份。
那年暑期輔導課的最後一天剛好是中元節前夕,由於只有一節課的考試,所以我比平常早了一班火車回家。正午的烈陽下整條山路沒有半個人影,但當我走近一座跨越山澗的小橋時,隱約地我好像聽到短促的人聲,不過分不出男女,也聽不清內容,而偏偏那個地點又是恐怖傳說最多的「歹所在」,所以剎那間我已被嚇出一身雞皮疙瘩。
那座用條狀的石板鋪成的橋不長,約莫才兩三公尺左右,當我一踏上橋,我就知道乾涸的橋下的確有人,因為我看到橋下的雜草叢裡露出一截竹扁擔,所以過橋的時候,我不自覺地、好奇地放慢腳步盯著石板縫隙往下看。
在正午直射的陽光下,我清楚地看到阿英的臉,而她的身體則被一個男人裸露的背部整個覆蓋住,而另一道縫隙裡,則出現豬肉擔子的局部。
我不知道阿英是否也同樣透過縫隙認出是我,然後像傳說中的鴕鳥會把頭埋進土裡,用「沒看見」來逃避已然無法逃避的危急那樣,我看到她很快地閉上眼睛,然後把頭往一邊側過去。
那一剎那的畫面始終留在我的記憶裡。
由於第二天是中元節,所以那天傍晚礦坑口特別熱鬧,因為在冰箱還不十分普遍的那個年代,村裡的人習慣把容易腐敗的魚、肉拿到溫度比較低的礦坑裡存放。
就在我掛好牲禮,並且在上頭做好記號正要離開的時候,我看到阿英也拎著一大塊豬肉走了過來。有人看了一下她手上的豬肉之後讚美說:「啊,妳挑的這一塊最好!那個死賣肉的說『胛心肉』沒貨,原來是被妳買走了。」
她毫無表情地從我身邊走過,而且就像根本不認識我一般,連看都沒看我一眼;而就在她走過之後,我卻忽然覺得輕鬆,雖然也有那麼一點點的失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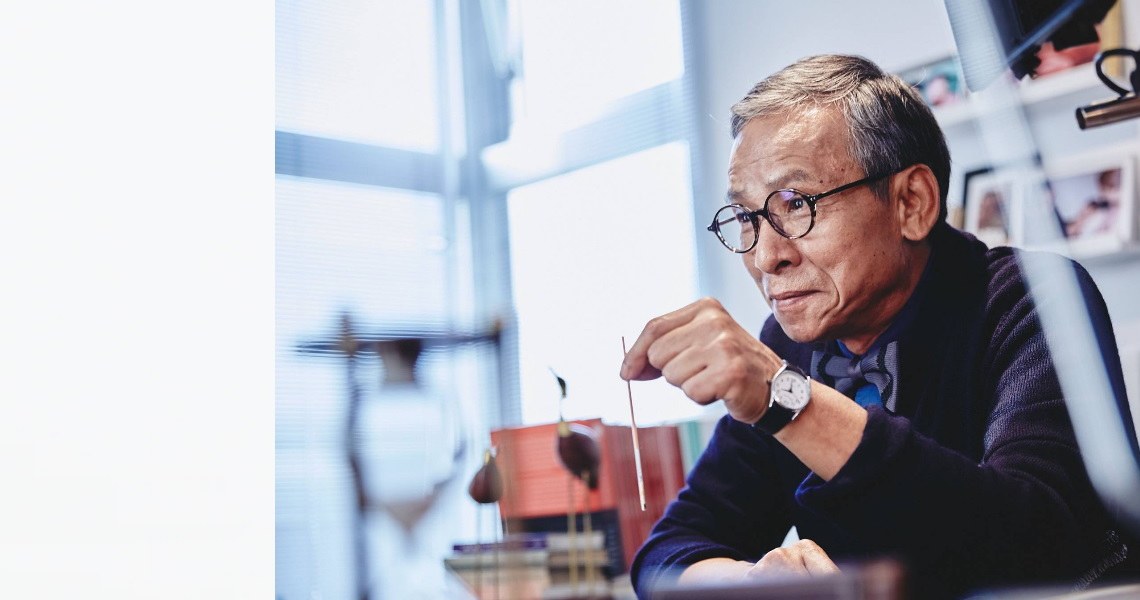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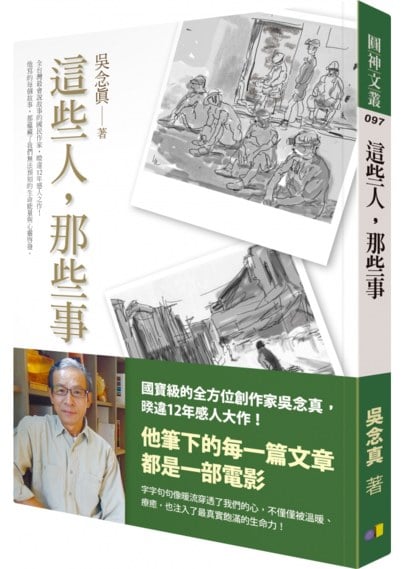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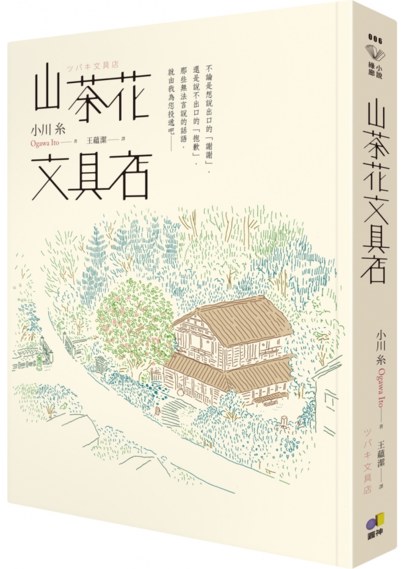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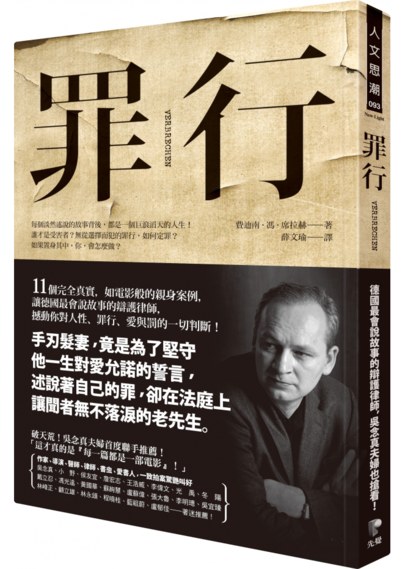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