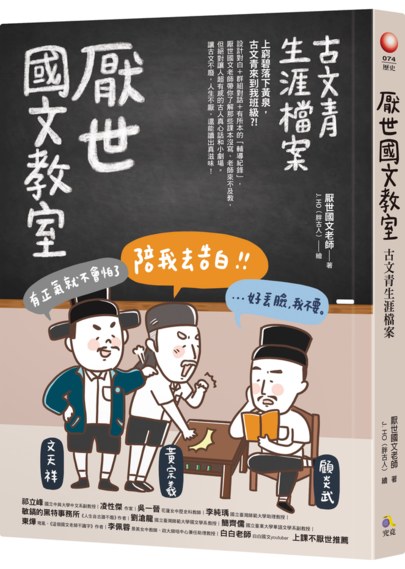1. 夢境
一大清早,如初睜開眼睛,就見到窗外那棵木蘭樹的枝椏上,在一夜之間冒出無數個小小如筆頭般毛茸茸的花苞。她縮在羊毛被裡,眼睛盯著樹梢,腦海裡卻閃過無數個模糊不清的影像—
花還沒開,她還來得及⋯⋯來得及做什麼呢?
影像突然扭曲變形,散成千萬個光點在眼前跳躍。如初頓時頭痛欲裂,眼眶發紅,不由自主地落淚。就在她痛到蜷起身子時,叩叩叩三聲輕響之後,木頭的格子窗迅速被推開,蕭練縱身跳了進來,腳下劍影一閃而逝。
他直接飛到床前,將如初抱進懷裡,伸出食指輕輕按在她的眉心之間。
一股冰涼感透進腦內,疼痛頓時減緩。如初長長地舒了口氣,蕭練低聲問:「又做惡夢了?」
她恍惚地點了點頭,喃喃說:「有光,在遠方⋯⋯」
沒有用,不管再怎麼努力,腦海中的畫面依舊迅速淡去。如初睜開雙眼,目光渙散地望著蕭練說:「還是一樣,什麼都記不住。」
雖然記不起夢中經歷,但那種眼睜睜看著摯愛墜入深淵,自己卻無能為力的憤怒悲傷,卻久久無法忘卻。
去年年底,她搬進這棟老公寓,跟蕭練成為樓上樓下的鄰居。
公司就在幾百公尺外,每天走路十分鐘上下班,日子過得平靜安穩,不時還會出現一些小驚喜。比方說巷口新開了一家好吃的麵店,又比方說他們在森林公園內發現一條淹沒在荒煙蔓草中的古道,只要在進入公園後避開人群踩上長劍,就能輕鬆飛越古道入口處的陡坡,直接進入林木蓊鬱、景色優美的路段,帶著零食跳下劍走兩三個小時,是週末踏青的最佳選擇。
快樂的高峰出現在春節假期,蕭練主動提議,要陪她一起回家過年。如初原本對這件事非常緊張,跟媽媽溝通再溝通,搞得全家都跟她一樣神經繃得死緊。然而到了她家之後,蕭練所展現的適應力,卻完全出乎如初的意料之外!
他跟著他們一起吃飯、看電視,陪爸爸評論時事,陪媽媽採購年貨,大年初一還陪他們到處拜年。無論走到哪裡,他的禮數周到,受到老一輩親戚們的交口稱讚,風度翩翩,更不時引起同輩與路人的注目。
離家前一天,如初索性拉著蕭練參加她的高中同學會,狠狠滿足了一次虛榮心—誰也不能阻止她炫耀男朋友太帥。
孰料年假過後,惡夢突然來襲,在短短不到幾天之內,就令如初從雲端跌落至谷底。
惡夢發生的原因不明,頻率也毫無規律可循,有時候一週才一次,也有時候好幾個夜晚接連不斷。而她每一次墜入夢境,都是不到筋疲力盡絕對無法醒來,但只要一醒過來,便立即將夢境內容忘得一乾二淨。
最近幾天又是惡夢的高峰期,如初靠在蕭練身上休息片刻,抬眼問蕭練:「你有沒有聽到什麼?」
他就住在樓上,兩人間只隔著一層天花板,以他的耳力,就算不留心,也能將她的動靜聽得一清二楚。這個能力在平常不時會讓如初有點尷尬,但是從她開始做惡夢起,反而變成安全感的來源。
蕭練垂下眼,回答:「跟前晚差不多。妳又喊了我的名字,有時候還壓低聲音驚叫,像是害怕被誰聽到似的。」
他的聲音有些沉鬱,但如初並未留意。她自言自語地說:「跟前晚差不多?也就是說,一直以來,我都在做同一個夢?」
「有可能。」蕭練頓了頓,忽地問:「妳會不會反覆夢到在劍廬跟犬神、封狼⋯⋯還有我⋯⋯對峙的那一幕?」
他的語氣帶著強烈的自責,如初一愣,馬上用力搖頭,說:「不可能。」
蕭練握住她的手,說:「初初,妳根本不記得自己做了什麼夢。」
「可是我記得夢裡的情緒。」如初反握住蕭練的手,急切地說:「我了解自己,如果夢到劍廬,我絕對不是這種反應。」
蕭練沒出聲反駁,但神色間卻流露出顯而易見的不同意,如初看在眼裡,不禁沮喪地問:「你不相信我?」
蕭練將她摟進懷裡,輕聲說:「我當然信妳,不過,別低估人類潛意識的複雜性。」
他的說法很有道理,卻完全無法說服如初。如初將頭埋在他的肩窩裡好一會兒才開口說:「蕭練,我要講一件事,你聽就好,不准發表意見。」
這話言詞上十分霸道,但如初用的口吻卻純屬撒嬌,蕭練忍不住嘴角微翹,答說:「好,妳說,我聽。」
「我總感覺,是這個夢主動找上我,而不是我在做夢。」
如初抬起頭,跟蕭練拉開了一點距離,鄭重地又說:「我剛剛想起來了,夢裡有一種鹹鹹腥腥的味道,像海⋯⋯這真的很奇怪,我以前做夢從來沒有嗅覺。」
蕭練欲言又止地望著她,如初嘆一口氣,抱起羊毛被認命地說:「我講完了,你想批評什麼就直接說吧。」
「嗯,初初,其實我想說的是,妳非常敏銳。」
蕭練對上如初狐疑的視線,溫柔地摸摸她的頭髮,又說:「我大嫂是心理學專家。她有一次告訴我們,做夢是人類大腦重組訊息的副產物,但因為嗅覺和味覺幾乎與大腦的皮層無關,所以也鮮少進入夢境。」他頓了頓,若有所思地說:「也許妳對,這個夢有問題⋯⋯」
「你有大嫂?」如初一臉震驚地傾身向前,問:「意思是說殷組長結過婚,為什麼我從來沒聽你們提起過?」
「過去三十年他們分居,我們大家都不方便提。」蕭練對如初眨眨眼,做出一個會心的表情。
如初自以為了解地點點頭,但還是忍不住好奇,湊近了悄聲問:「他們真的結婚了?」
蕭練點頭:「有證書,民國政府發的,證書上還寫了什麼『三生石上注姻緣,恩愛夫妻一線牽』之類的詩詞。」
這太浪漫了,如初喃喃:「好想看殷組長的婚紗照,民國新娘耶⋯⋯」
「吵架的時候撕光了。」
「你很殺風景欸。」
「實話實說而已。」
今天是週末,不用上班,兩人靠在一起聊了片刻,如初伸手掩住嘴打了個呵欠,呻吟著說:「好累。」
她的眼睛還有點浮腫,嘴唇乾裂,顯然被惡夢折騰得不淺。蕭練憐惜地看著她,建議:「等下我們去國野驛吃頓豐盛的早午餐,好不好?」
「國野驛有早午餐?」如初問。
蕭練肯定點頭:「今年開始提供的,我有特別向邊哥打聽過。」
如初更加不解:「你為什麼會去打聽這個啊?」
他不需要進食維生,對吃也沒有任何興趣。
蕭練用指頭點點她的鼻尖,說:「妳搬進來那天我就說過,我的學習能力不強,但始終不間斷,看來妳沒聽懂,我說的『學習』兩字,是特別指當妳男朋友這點。」
如初開心地笑了,索性翻個身,整個人窩進蕭練的懷裡。晨風微涼,他扯起羊毛被裹住她,啪地一聲,一本線裝書從被子裡掉落到枕頭上。
那是記載了傳承的古書,蕭練凝視書封片刻,忽地問如初:「妳的惡夢會不會跟傳承有關?」
「我有想過這個可能性,可是開啟傳承之後,我就算在夢裡進入傳承,醒來後也能記得內容,跟最近的情況完全不一樣。」如初在他懷裡翻個身,仰起頭又說:「話說回來,如果傳承的目的是為了傳遞經驗跟知識,那讓人記不住的夢,豈不是一點用都沒有嗎?」
蕭練沉思片刻,並未回答她的問題,卻再問:「妳最近花很多時間在研究解除禁制?」
這是他們一直以來的矛盾,爭辯過幾次之後如初就決定再也不跟蕭練討論禁制的事了。
今天也不例外,她抓起羊毛被裹住自己,試圖用嬌嗔的語氣轉移焦點:「隨便看看書而已。你先出去,我要換衣服了。」
「什麼書,妳開啟新的傳承了?」蕭練不為所動地追問。
「當然沒有,你以為傳承是貓罐頭,想開就開呀?」如初指著房門說:「快點,我快餓死了。」
蕭練這才放下心,站起身用嘴唇輕觸她的額頭。他的動作優雅,需要仔細看才能發現與她刻意保持了一點距離。如初瞥了蕭練胸前一眼,纏繞在心臟部位的鎖鏈一如往常般游移閃爍,散發著淡淡金光。
在這條鏈子所代表的禁制尚未解除之前,他需要控制情緒,不能過度使用異能,與她的肢體接觸更是需要小心。誰也不知道觸發劍魂取代意識主宰蕭練身體的界限在哪裡,然而只要一旦越界,代價便有可能是死亡⋯⋯
她的死亡。
由他親手執行。
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決定在一起。
共同的決定。
晨風很輕,有一下沒一下地掀動著薄紗窗簾,氣溫逐漸回暖,一隻燕子啾啾叫著飛過窗前。也許是因為天氣變好,又或者是因為從惡夢裡醒來,就能看到親愛的他,如初打從心底感覺全身都暖洋洋的。她目送蕭練踩著劍,腳不沾地低飛出房門,躺回枕頭閉上眼睛,數一、二、三,然後迅速掀開被子跳起來,衝到衣櫥前拉開抽屜找毛衣。
十五分鐘後,如初梳洗完畢,換上精心挑選的外出服,噔噔噔地樓梯走到一半,便見蕭練站在牆壁上掛著的一幅卷軸前面,抱胸沉思。
這幅畫是鼎姐送的。有一次鼎姐來拜訪,看到她的住處一點擺設都沒有,回去之後便硬是從老家的收藏品中挑了一幅類似《清明上河圖》的古代風景畫給她,還特別聲明了這幅畫無人落款,就筆觸判斷也非出自名家,要如初放心收下,別因為是古物就不敢拿出來掛。
畫中主體是一個熱鬧的市鎮,亭臺樓閣林立,中間點綴著小小的人物,有小販沿街叫賣,婦女坐在轎子裡掀起窗簾看熱鬧,也有士兵騎在馬上過拱橋等等。遠方海水粼粼,靠海處種了一整排的防風林,佛塔巍然聳立在防風林的後面,一派繁華景象。
為了照顧這幅畫,如初還特別去請教在博物館工作的同學,選了不會被陽光晒到的牆面懸掛,又買了一部除濕機擺附近,控制濕度外加定時除塵,確保畫作不會受到損傷。
如初見蕭練神色嚴肅,心一驚,三步併作兩步跑到他身旁,急問:「畫怎麼了嗎?」
「沒什麼。」他伸手扶了扶畫,又說:「有點歪,跟我昨天看到的位置不一樣。」
一隻圓滾滾的黃貓從沙發底下鑽出來,走向他們。牠先到如初腳邊蹭了蹭,接著轉向蕭練,耳朵貼著腦袋,弓起身,露出牙齒狠狠嘶了一聲,這才迅速跳到靠牆放的一張椅子上,張著一雙金黃色的眼睛看如初,眼神無辜至極。
隨著貓咪這麼一跳,椅子晃了晃,碰到卷軸的底部,畫又歪了。
「喬巴!」如初走過去抱起貓,氣惱地輕彈了牠的耳朵一下,說:「又這樣,壞貓咪。」
喬巴比三個多月前長大不少,身上的虎斑紋路益發鮮明,已經具備成貓的架式。然而隨著體型變大,牠卻像是忘記蕭練曾經救牠一命似地,每次只要如初在場,就對蕭練張牙舞爪,一臉囂張,但倘若如初不在,喬巴看到蕭練總是一溜煙就躲起來,連聲喵都不敢吭。
喬巴不服氣地抬起頭咪嗚咪嗚地叫,像是在抗議,蕭練不以為意地說:「不怪牠,小動物一般都會避開我,我身上的金屬氣息對喬巴來說,肯定代表危險訊號。」
「所有動物見到你,本能上都會先怕你嗎?」如初問完,馬上搖頭,說:「我就不會,第一次見面我還覺得你滿親切的⋯⋯因為我是修復師的關係?」
蕭練搖頭:「沒人天生下來就是修復師,經過訓練之後的不害怕,只是壓抑本能而已。坦白說,這輩子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用『親切』兩字來形容我⋯⋯妳確定沒記錯?」
「當然。」她怎麼可能記錯這個,如初毫不猶豫回應。
「天生如此?」蕭練注視著她,說:「我想不出緣故。」
他的語氣一本正經,但眼神太過溫柔,聽在如初耳朵裡,自動被轉譯成「我們是天生一對」的情話。
如初開心地朝蕭練笑笑,眼角餘光瞄到喬巴偷偷摸摸地又要跳椅子,馬上一把撈住貓,對蕭練說:「你等我一下。」
她的口氣有點兇,蕭練不解地後退一步,只見如初將喬巴抱到卷軸前,用同樣語氣衝著貓耳朵說:「罪魁禍首,要懂得欣賞藝術,不可以暴衝。」
喬巴不安分地亂扭,蕭練揚眉,問:「教育有用?」
「希望有用。」如初彎腰放下貓,往前邁一大步,握住椅背,又說:「在那之前,我們先把椅子移開。」
蕭練看著如初認真的背影,忽地一陣衝動,上前說:「我幫妳。」
「好啊,但其實我拿得動⋯⋯」
她住了嘴,看他將椅子放到餐廳擺好,順手幫貓加乾糧,又換了一碗乾淨的飲水,舉止之間充滿愉悅。
在這短短幾分鐘內,他只是個居家的男人,而非一柄劍。
過去幾日陰雨綿綿,好不容易今天放晴,大家都跑出來了。蕭練開車上路後沒多久,就遇上塞車,窗外薄霧飄忽,將整個城市點綴得迷迷濛濛,如初拉下車窗想透口氣,這才發現霧非霧,而是行道樹剛萌芽的新葉絨毛脫落,隨風四散,造成了這幅景象。
路上的行人與腳踏車騎士大多戴著口罩,如初沒過多久也覺得鼻頭發癢。她趕緊關上車窗,轉頭問蕭練:「你不會過敏吧?」
蕭練笑著搖頭,如初好奇地再問:「那你會做夢嗎?」
這個問題似乎讓他有些困擾,蕭練躊躇片刻,最後說:「我們不睡覺,所以,如果妳問的是因為受傷過重而無法化形、失去意識的那種時刻,答案是不會。」
「那,入定的時候呢?」如初還記得這個詞,這是他們特有的休息方式,代表人形消失,意識回到本體之內。
蕭練沉默了一會兒才回答:「在那種狀況下,偶爾會有些回憶畫面閃過。」
「回憶不是夢。」如初不太明白蕭練為什麼要將兩者相提並論。
「失真的回憶、扭曲的回憶,某些面孔被無限放大,一個小動作被不斷重播,清楚到即使以我們的能力也不可能觀察得如此之細。等時間拖得夠久,當事者都已不復存在之後,你漸漸懷疑事情是否真實發生過,或者只存在於想像之中。」
講到這裡,蕭練頓了頓,嘗試著將語氣放得輕快些,又說:「我的記憶力並不比一般人強,幾百年前的事情偶爾回憶起來,也就像夢一樣了。」
「了解⋯⋯」如初咬了咬嘴唇,低聲說:「對不起。」
「為什麼?」蕭練轉頭凝視她。
「因為,讓你難過了。」如初其實並不確定理由,但她直覺認為,這個對她來說無關痛癢的問題,會讓蕭練十分介意。
他靜默片刻,輕輕喚她的小名:「初初?」
「在。」她像課堂上被老師點到名似地,乖乖舉起右手。
「如果妳的交往對象是一個普通人⋯⋯妳也會需要道歉嗎?」
不是這樣的。如果對方是個普通人,她也許不需要為這個問題而道歉,但只要相處下去,總有一天,她會需要為一個她自認沒什麼但對方卻很在意的問題,說上一句「對不起」。
重要的是,因為愛,她並不介意說上這句對不起,一點都不。
但顯然,他介意聽。
如初的眼神掠過一絲黯然。蕭練看到了,卻沒有看懂。他摸摸她的臉頰,說:「下一次,別因為我們之間的差異而說對不起,那才真會讓我難過,至於夢,對我而言,只是一些遙遠到早該遺忘的過去而已。」
他的語氣太溫柔,如初順從地點點頭,決定先不澄清。
只要相處下去,有一天,他會懂。而她相信,這一天,並不遙遠。
車子開進國野驛的停車場,如初跨出電梯,還沒走到櫃檯,便透過落地的玻璃窗,瞥見庭園中的水池畔,有十來隻水鳥圍繞在一名身材高挑的男子周圍,嘰嘰呱呱地討東西吃,中間居然還混進了一對色彩鮮豔的鴛鴦,熱鬧異常。
那名男子年約三十來歲,一頭及肩長髮,滿臉落腮鬍。他慢吞吞地從紙袋裡取出麵包屑餵鳥,三不五時抓抓頭,彷彿是一名拓落不羈的藝術家。
然而春寒料峭,這位大叔卻只穿了一件上面畫有卡通圖案的圓領短袖T恤,連薄外套都沒披,怎麼看怎麼奇怪。如初忍不住朝他多瞄了幾眼,下一秒,大叔抬起頭,兩人視線相撞,他居然朝她咧開嘴笑了笑,眼神在友善中帶著好奇,彷彿也想知道她是誰似地。
如初有點窘,趕緊也朝大叔禮貌性地微笑,然後就感覺右手突然被蕭練緊緊握住⋯⋯
「他控制了自己的氣息,因此鳥不僅不怕他,還可能把他當成同類對待。」蕭練的表情沒什麼變化,只用淡淡的語氣如此解釋。
所以這又是一位化形者。
如初問:「你認識他?」
「不算朋友。」
這句話的含意頗深,如初頓時提高了警覺,她往蕭練身邊靠了靠,忍不住又看了大叔一眼,正好瞥見他在伸懶腰,露出一截古銅色的腹肌,雖然身材精壯,但面容純良,一副人畜無害的模樣。
不是朋友,但也不算敵人?
邊鐘從櫃檯裡轉出來,也瞄了大叔一眼,沒好氣地說:「這傢伙就是不務正業,說好以工代宿,白吃白住了一個多月,連張桌子都沒擦過,混蛋。」
最後兩個字邊鐘提高了音調,大叔聽見,懶洋洋地朝他們揮揮手,說:「聽到了,小邊鐘。」
他又掏出一把麵包屑,繼續餵鳥。邊鐘翻了個白眼,轉回頭問如初:「今天就只有一種選擇,全天候供應的英式早餐,妳行嗎?」
如初對吃本來就不挑剔,她無所謂地點點頭,順口問:「為什麼只有一種?」
「因為主廚辭職不幹了。」邊鐘攤手,一臉無奈:「再聘不到人,我考慮連餐廳都收起來,只提供住宿。」
「那太可惜了。」如初脫口而出。
「可不是。所以我正努力說服一個自閉一百年的傢伙出山掌勺—」
噹噹,邊鐘的手機訊息鈴聲響起。他抓起手機看了兩行之後,丟下一句「我忙,你們自便」,扭頭就往廚房走去。
「一百年⋯⋯」如初眼睛一亮,轉向蕭練問:「如果邊哥成功聘到主廚,我們有可能吃到一百年前的菜色嗎?」
蕭練唔了一聲,說:「我吃不出來有任何差別。」
「⋯⋯對不起。」
「這次又是為什麼?」
「找你討論菜色,我的錯。」
蕭練一臉無語,如初則因為自己小小的報復成功而十分得意,總之,戀人間的絮語,即使意見不合也甜蜜。侍者走過來帶位,等他們坐好後又立刻奉上熱茶與手工麵包,並殷切詢問他們甜點喜歡藍莓或是巧克力杯子蛋糕。
國野驛一向隨季節更換布置,今天插在桌上的花是雪白的雛菊,襯著薄荷綠的餐桌布,將整個空間點綴得清新自然。
早餐很快便送上桌,大盤子上堆滿香腸、培根與馬鈴薯泥,煎蛋一口氣給三顆,跟以往的精緻風格大異其趣,味道並沒有之前豐富,但嘗起來還是很不錯,看得出來廚房人員在缺主廚的情況下,努力做出彌補。
他們坐在靠窗的桌旁,大叔已不見蹤影,水鳥也散得七七八八,倒是飛來一大群麻雀,在地面的縫隙裡翻撿覓食。水池旁栽種了一圈鬱金香與風信子,紫白相間,映著陽光盛開,讓整個庭園更顯得生氣勃勃。
當侍者再度走上前,幫他們將茶壺添滿熱水時,蕭練忽然抬起頭,望向門口。如初跟著回頭,瞧見鏡重環穿著白色毛衣、藏青色短裙與黑色長筒襪,拉了一個小行李箱,一副學園少女的打扮,施施然從門外走進來。
如初趕緊低下頭,用力過猛,鼻子差點碰到盤子裡的馬鈴薯泥。但沒有用,重環環顧了一圈,直直走到他們桌旁,拉開椅子坐下來,跟蕭練「嗨」了一聲,然後轉過頭,歡樂地告訴如初:「今天好多人拍我。」
「動漫展嗎?」如初問,眼神不由自主地閃躲。
「這次的規模特別大,好多國際團隊都來參加,我看到一群老外cosplay天空之城,還原度超高⋯⋯妳最近是不是在躲我?」重環神色天真,話語卻犀利得不得了。
如初尷尬地笑笑,說:「那個,鏡子,妳本體上的鏽斑,我還是找不到辦法消除。」
「噢,那奇怪了,我感覺有進步。」重環捧著半邊臉,歪頭說:「牙痛最近很少發作,妳什麼處理都沒做嗎?」
「我怕損傷鏡面,只敢抹一層灰錫粉然後用毛氈布打圈擦,這還是《淮南子》裡記錄磨銅鏡的土方法,不過你們個別對不同試劑的敏感度都不一樣,像鼎姐就對灰錫粉完全沒感覺⋯⋯」講到這裡,如初也有些振奮。她傾身向前,認真問:「但妳覺得有效是嗎?」
「還不錯,妳繼續擦,就算沒辦法治本,先治標我也OK。」重環不在意地揮揮手,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在如初與蕭練臉上轉了兩圈,又嗤嗤笑著問:「妳搬到他樓下之後就睡眠不足?黑眼圈好明顯。」
過去一個禮拜,公司裡有好幾名同事都關切過她惱人的黑眼圈,卻只有重環問得如此曖昧。蕭練挑起眉,如初趁他開口前飛快說:「做惡夢。」
「什麼惡夢?」重環追問。
如初簡單解釋了來龍去脈,重環用手撐著頭,饒有興味地說:「夢境的內容我也看不到,不過如果妳想知道自己潛意識裡最大的恐懼,也許我能幫得上忙。」
「怎麼幫?」如初摸不著頭腦地問:「妳的異能不就是『看透』跟『看遠』?」
「『看透』啊。」重環比了一個雙引號手勢,又說:「我現在身體健康了,能力當然跟著升級。不過這項異能目前還是被動的,妳得看著我的眼睛,心裡默唸要看到內心深處,才會有情境反射出來。從頭到尾就妳一個人看得見,至於景象能夠有多清楚,取決於妳對自己的心,有多誠實。」
「看這個沒什麼意義,畢竟,妳的惡夢未必是妳的恐懼。」一直沉默的蕭練忽地開口,對如初說:「而且,人所害怕的東西也會隨時間改變,妳今天看到的情景,未必是妳明天的恐懼。」
「你只試了那麼一次,什麼都沒瞧見,有什麼資格批評?」重環一撇嘴,小聲抱怨。
如初轉頭對蕭練說:「我懂,可我還是想試試看。」
「值得嗎,這個惡夢有這麼重要?」
「值不值得我不確定,但直覺想把它弄清楚。」
蕭練不再言語。如初轉向重環,問:「什麼時候可以進行?」
「沒什麼大不了的,哪時候都行。」重環攤手,又說:「按理說沒有危險也不會有後遺症,不過如果妳怕的話可以設個時間,比方說三分鐘一到,不管怎麼樣我們都叫醒妳。」
「就這樣,三分鐘。」蕭練按住如初的手,說:「答應我。不管看到什麼都告訴我,我們一起面對。」
明明是她的恐懼,他卻比她還戒慎小心。如初反握住蕭練的手,乾脆地答了一聲「好」,心裡卻有些不以為然。
她當然知道蕭練在擔心什麼,但蕭練失控這件事,會是她內心深處最大的恐懼嗎?
如初相當懷疑。
她喝下小半杯伯爵茶,做了幾次深呼吸,鼓起勇氣,看向鏡重環黑黝黝的雙瞳,在心底不斷默唸:「請讓我看見心底最深的恐懼,請讓我看見心底最深的恐懼,請讓我看見心底最深的恐懼⋯⋯」
慢慢地,一團朦朧的光暈將她包裹在其間,周遭的聲音如潮水般緩緩退去。等光暈消散,如初赫然發現她回到現在住的小公寓,就站在電視機前面。
不、不太對,空間格局雖然一模一樣,但許多地方都起了變化。剛粉刷過的白牆出現斑駁的水漬,去年年底才買的餐椅也變舊了,上面的布坐墊憑空多出好幾道縫補痕跡,沙發旁則多出一部媽媽老唸著要她買,說冬天吹了對關節好的小型電暖器。如初環顧左右,確定最大的變化發生在廚房,鍋碗瓢盆與瓶瓶罐罐都變多了,流理臺上擱著一個玻璃瓶,裡頭裝滿各式她最愛吃的手工餅乾。
這裡怎麼看都是個溫馨舒適的小窩,恐懼在哪裡?
一陣低沉的貓叫聲傳來,如初快步走到陽臺,看到木製的貓咪樂園還在,只是陳舊許多,一頭毛色已失去光澤的老黃貓窩在一件舊毛衣上直喘氣,眼睛滲出淚痕,瞳孔一點一點放大,顯然正逐漸喪失生命。
「喬巴!?」
如初撲上去,邊摸貓咪邊抽出手機,準備打電話給獸醫。然而一舉起手機,她便發現自己的手也變了,皮膚上多了好幾道結疤後留下的痕跡,指節也比印象中的粗,有一枚指甲裂了開來,似乎是舊傷復發,還纏著OK繃。
這是一雙經歷過滄桑的手,值得驕傲,卻不該屬於她。
如初放下喬巴,慢慢直起身,再度舉目四顧。
牆上又添了兩三幅畫,地上也多鋪了一塊小地毯,但餐桌上的杯子並不成對,面對電視的沙發椅是單人座。
她應該在這間公寓裡住了很久很久,一個人、一隻貓。
臥室有面穿衣鏡,如初走上樓,打開衣櫥,不意外地在鏡子裡看見一名身材依然苗條的中年婦女,神情理智冷靜,跟現在的自己很像,卻又不太像。不過話說回來,她很少照鏡子,也不太有機會好好看自己。
鏡子裡的人皮膚還很好,臉龐並不顯老,但頭髮卻參雜了許多銀絲。這應該是遺傳,聽媽媽說,爸爸年輕時就有少年白。
她出神地摸了摸鏡子,忽地想到喬巴,又急忙跑下樓去。然而來不及了,喬巴還是躺在原地,維持同一個姿勢,然而那個毛茸茸的肚子不再淺淺地一上一下。如初抱起牠,坐在地板上,夕陽斜射進屋內,窗外不時傳來車聲與人聲,懷裡的小身體仍有餘溫,但她的心卻一點點變冰涼。
蕭練在哪裡?
她彷彿坐了一整個世紀,直到聽見有人在耳邊喊「時間到」,如初又花了點力氣,才終於睜開雙眼。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窗外明媚到刺目的陽光,如初反射性舉起手遮住眼睛,然後才看見蕭練就在她身旁,神色滿是關心。
「妳看到什麼了?臉一直木木的,不像是害怕。」重環湊上前問。
要告訴他們,她看到四十歲的自己,孑然一身,在宿舍裡抱著相伴二十年的老貓,感覺牠的體溫一點一點流逝?
如初放下手,喃喃說:「我看到喬巴去世了。」
「那誰啊?」重環問。
「我的貓。」如初答。
重環哈一聲,說:「最大的恐懼就是養的貓死掉?妳的人生還真甜。」
如初垂下眼,不作聲,蕭練沉聲問:「出了什麼意外,有人闖進妳住處?」
如初搖頭,掙扎著坐直了,答:「沒有,就,老了⋯⋯我看到二十年後的我。」
「就這樣?」蕭練皺起眉頭,彷彿十分困惑。他頓了頓,問:「妳沒看到我?」
「沒有。」
如初看進蕭練的眼底,發現他是真的不懂。
也對,他經歷過那麼多死生戰場,她太過平凡的恐懼,他無從了解起。
涼意又從心底冒出來,如初扯緊外套,輕聲喃喃說:「我的未來沒有你。」
「這個,應該是我心底最深的恐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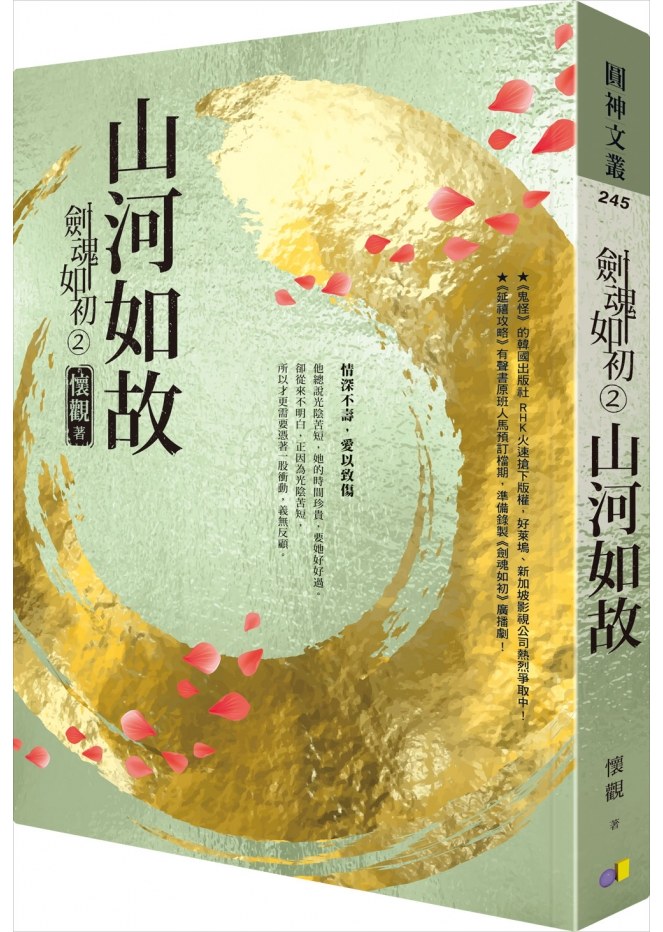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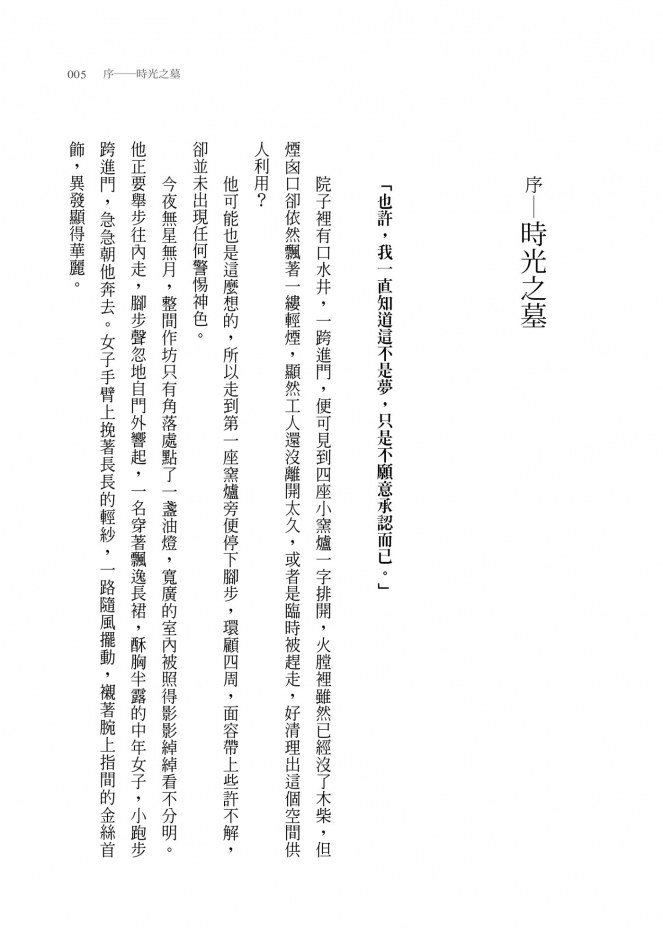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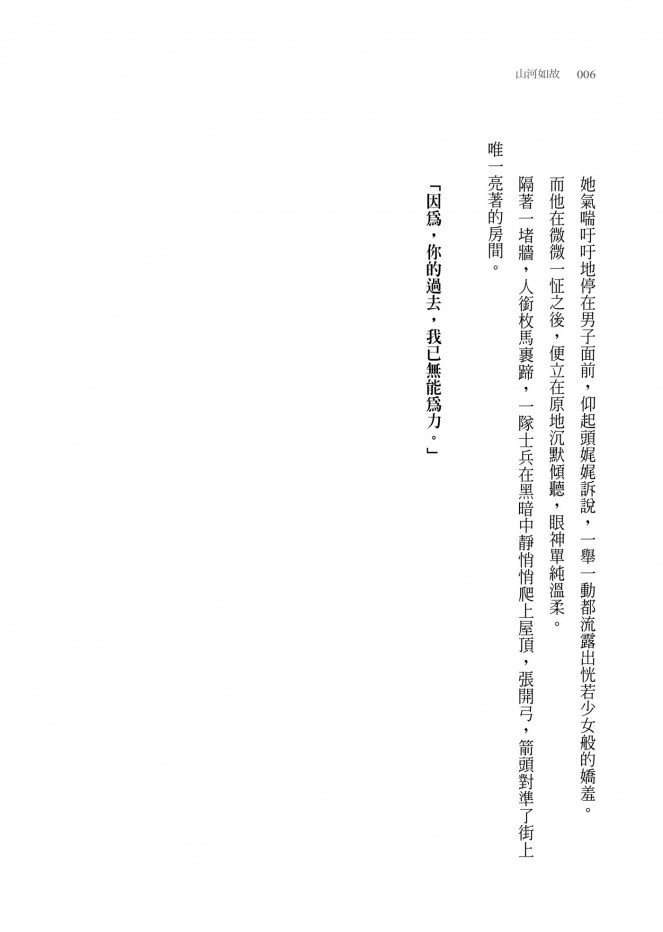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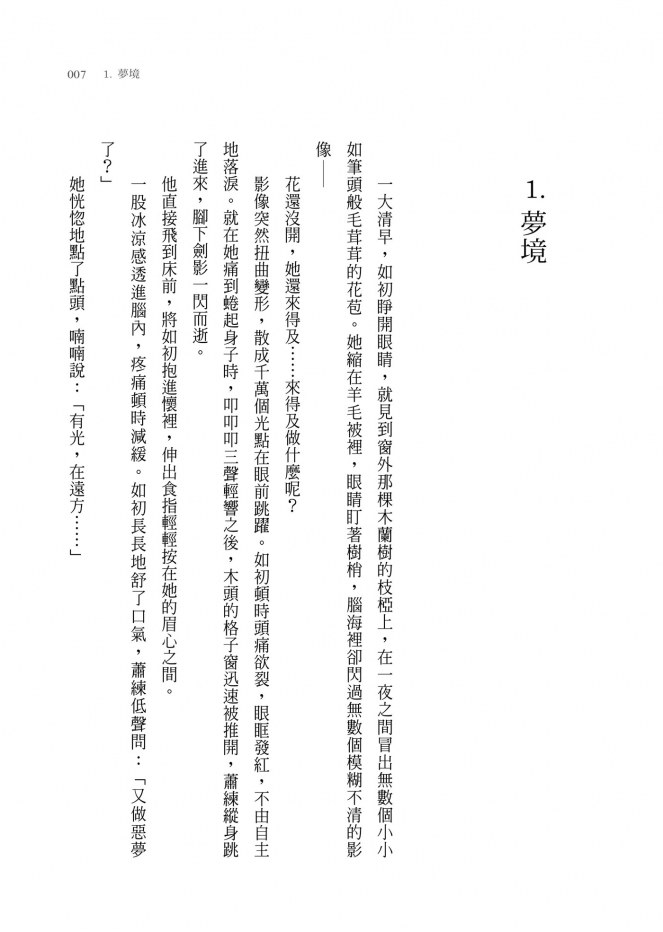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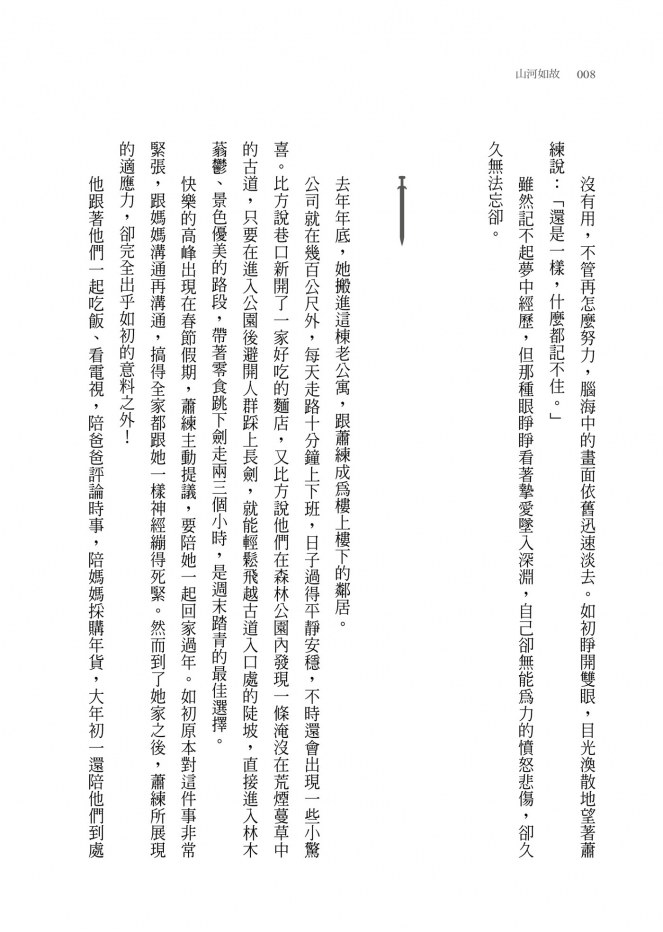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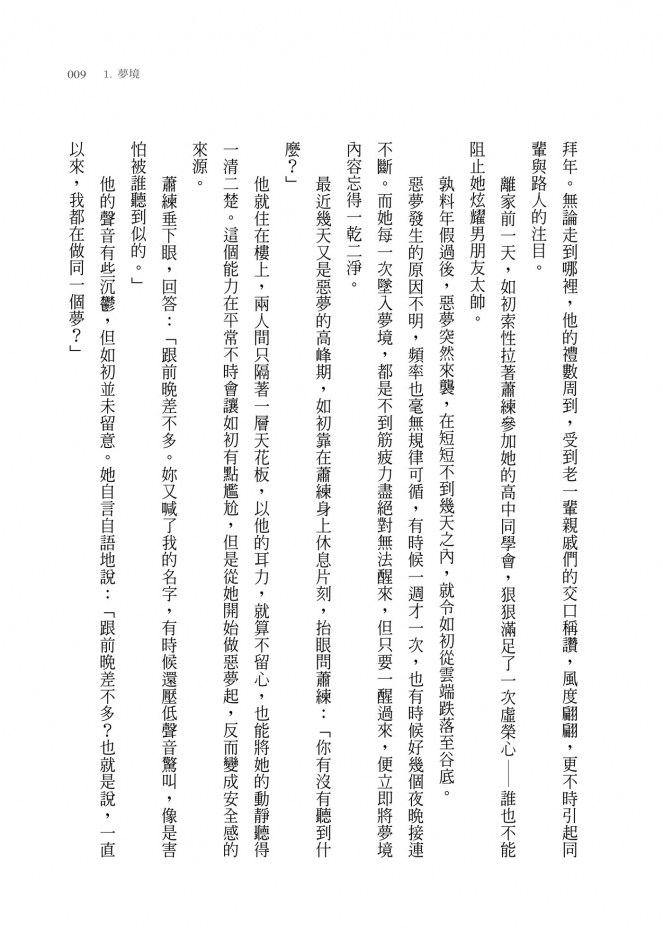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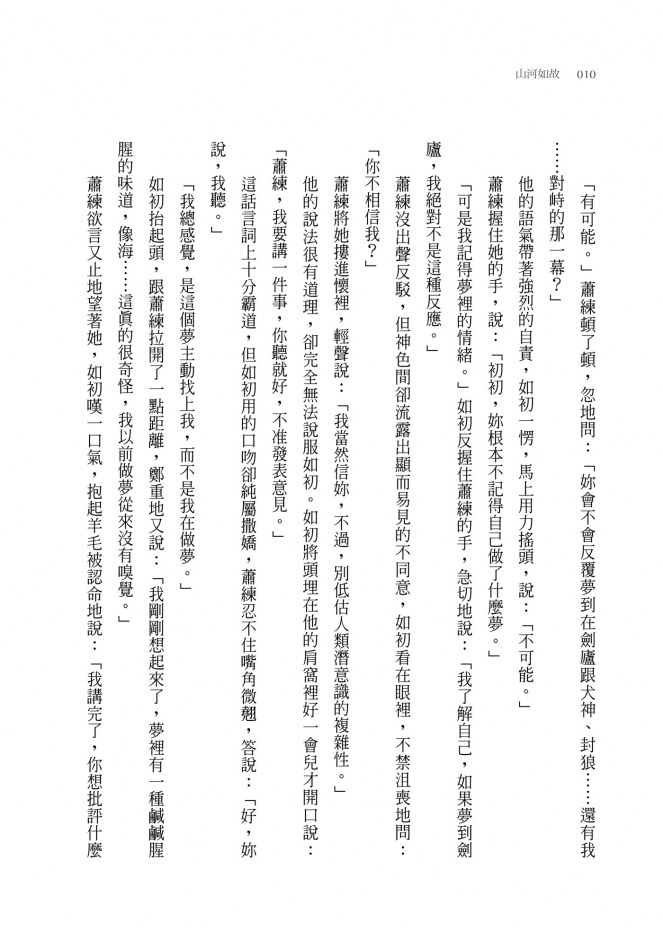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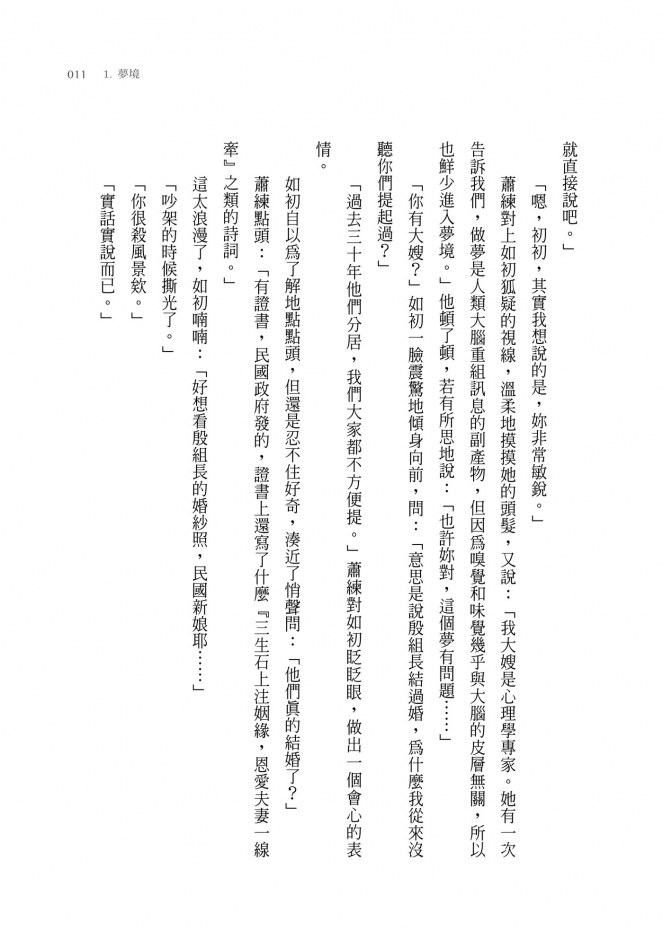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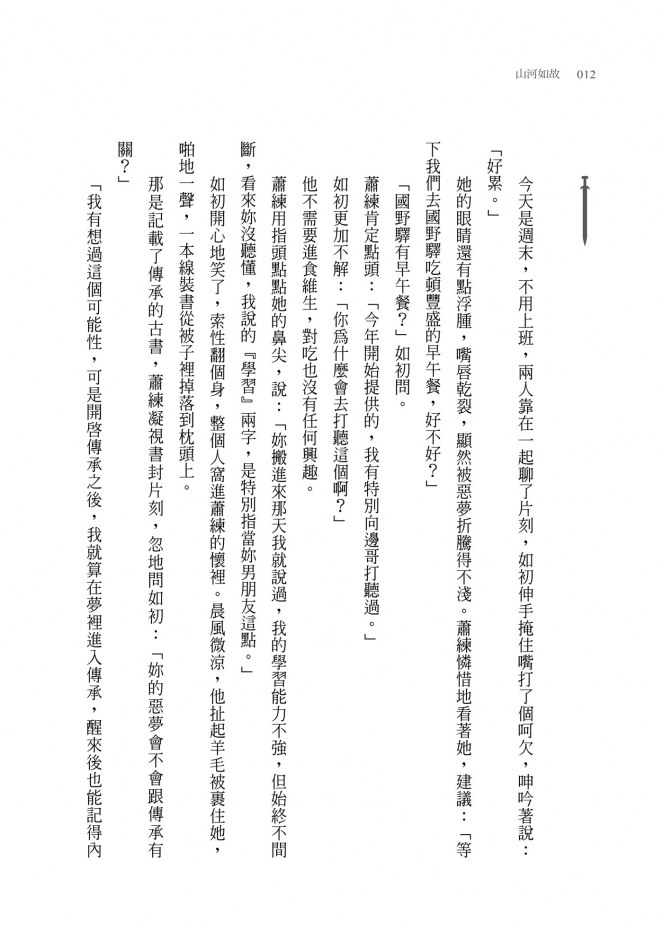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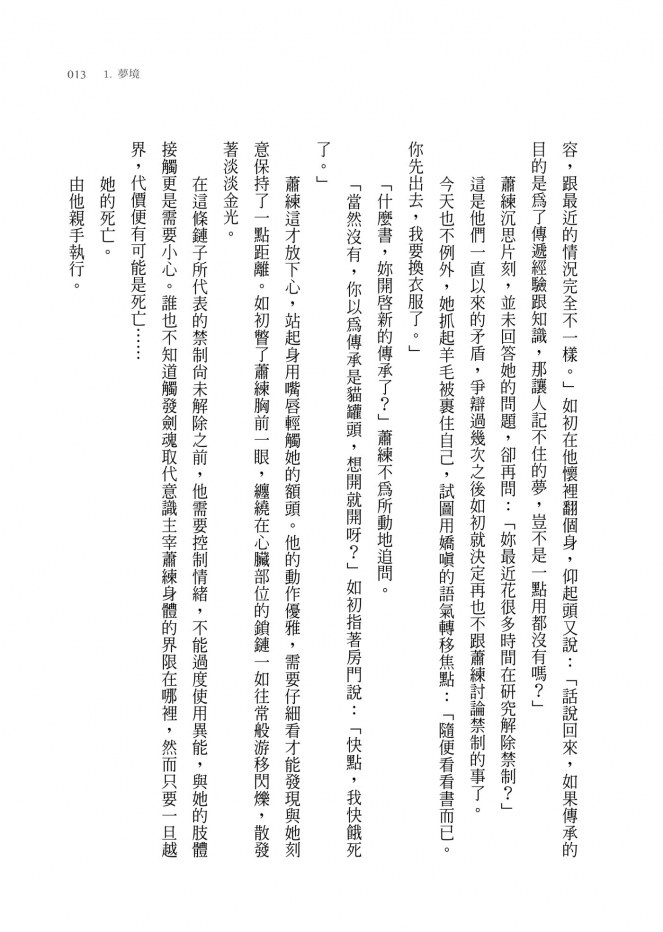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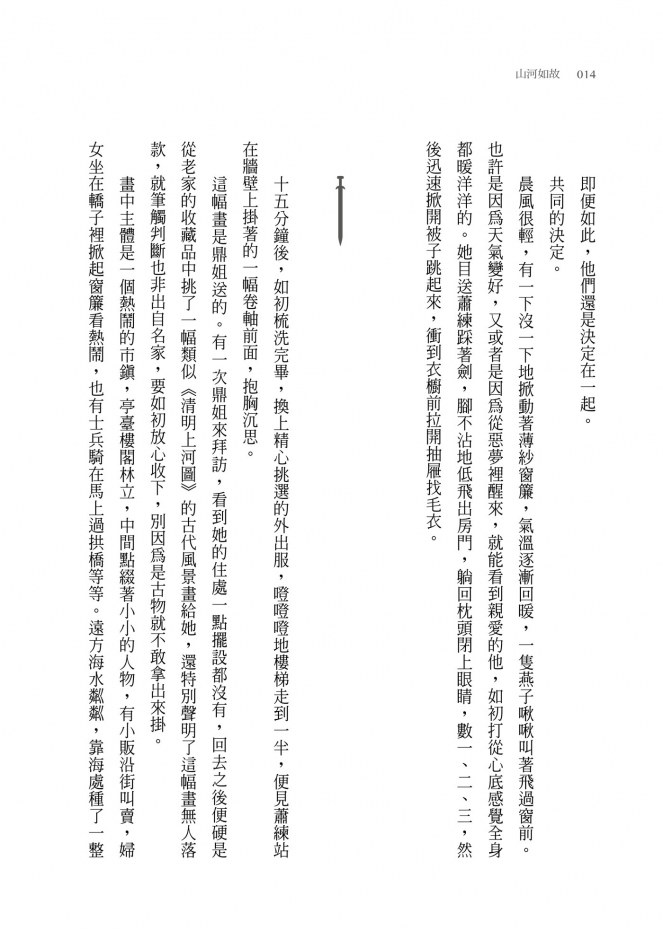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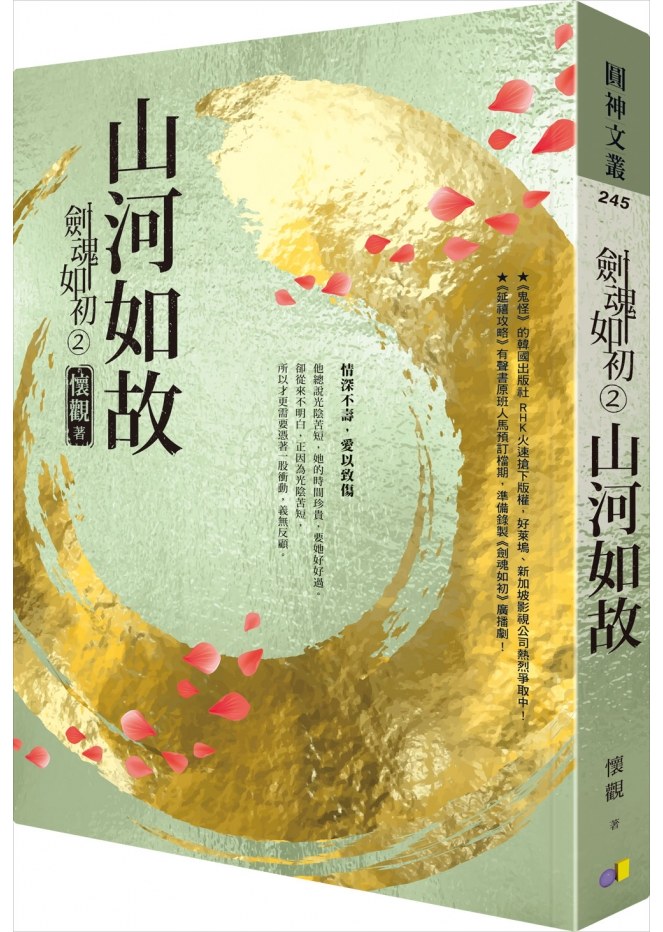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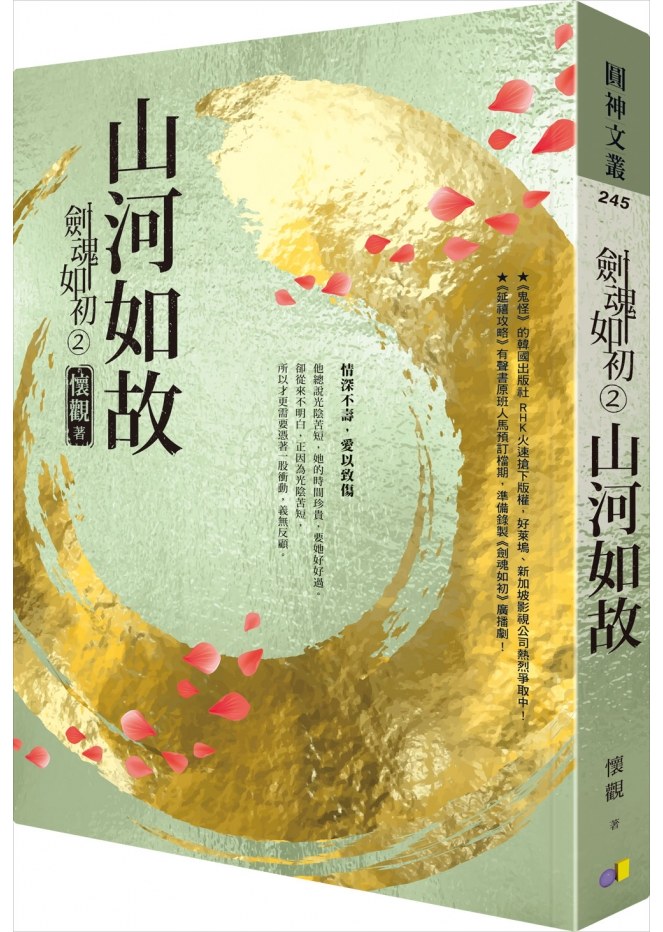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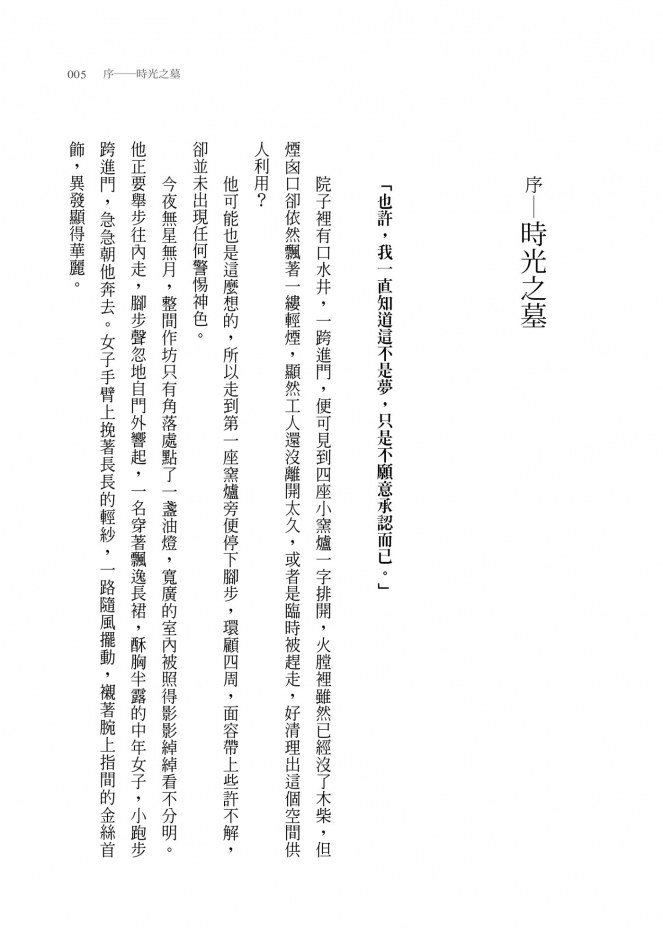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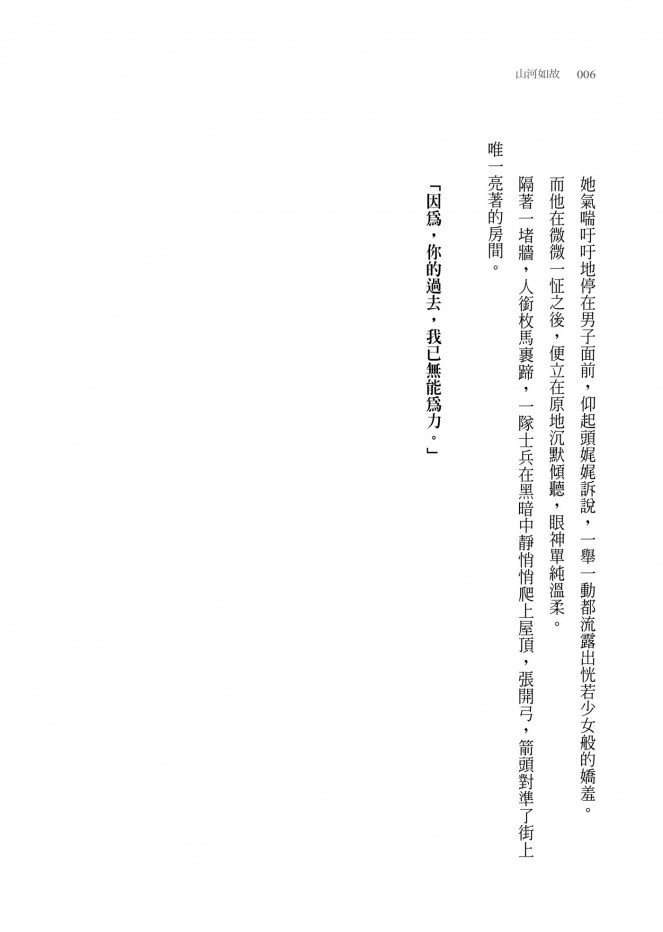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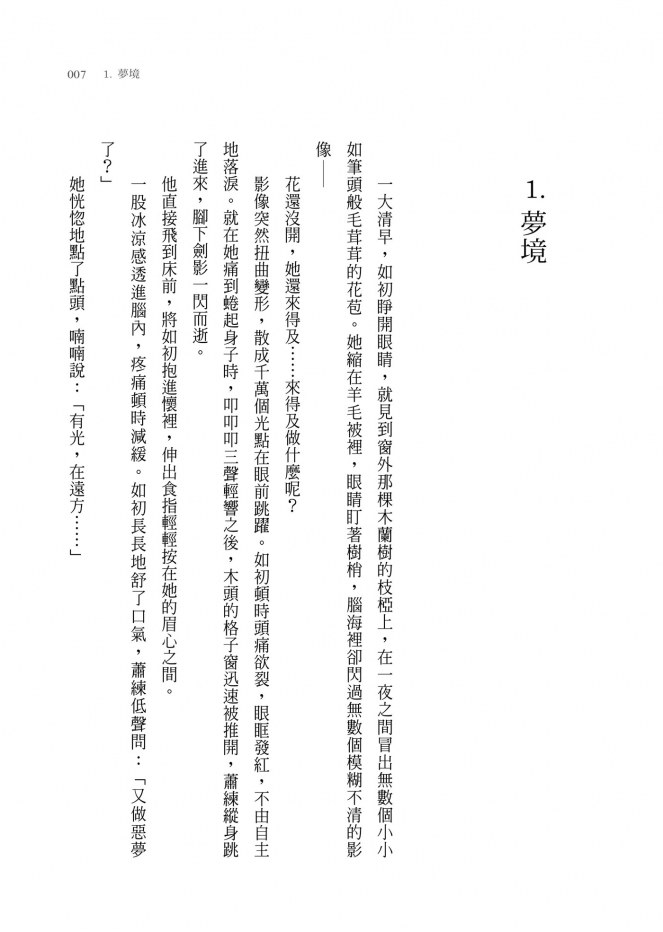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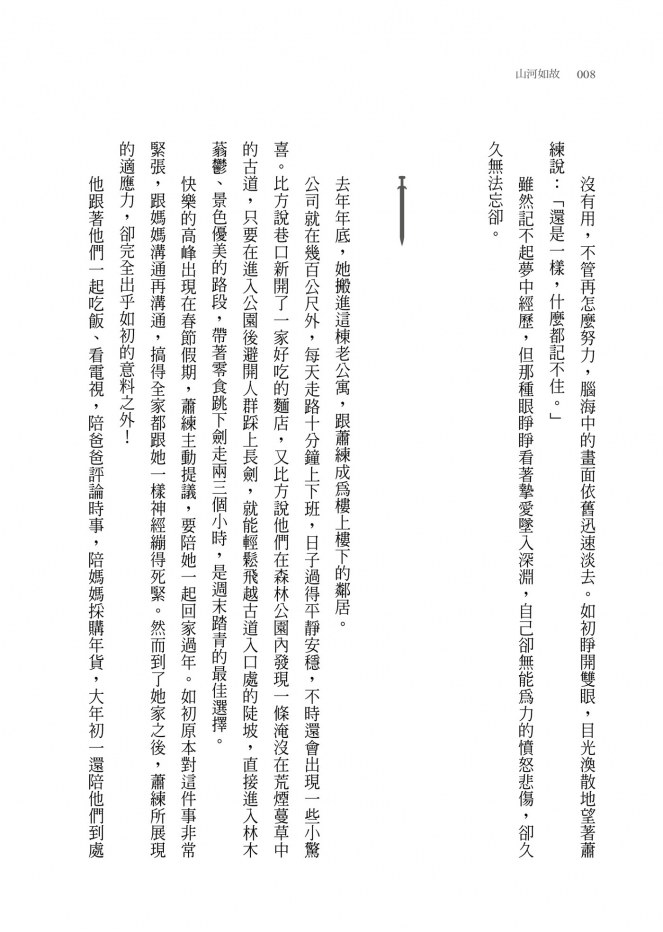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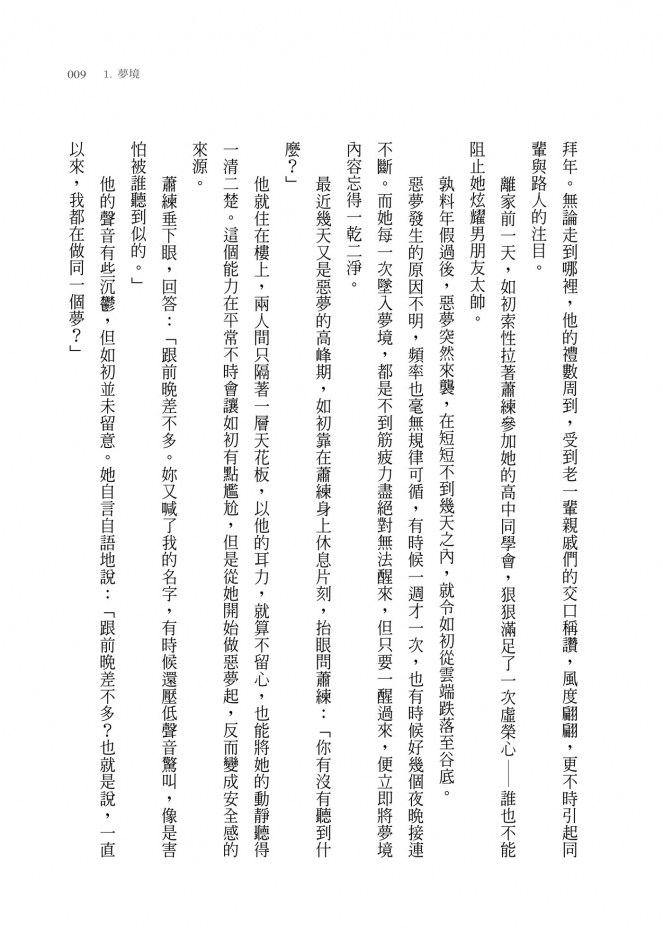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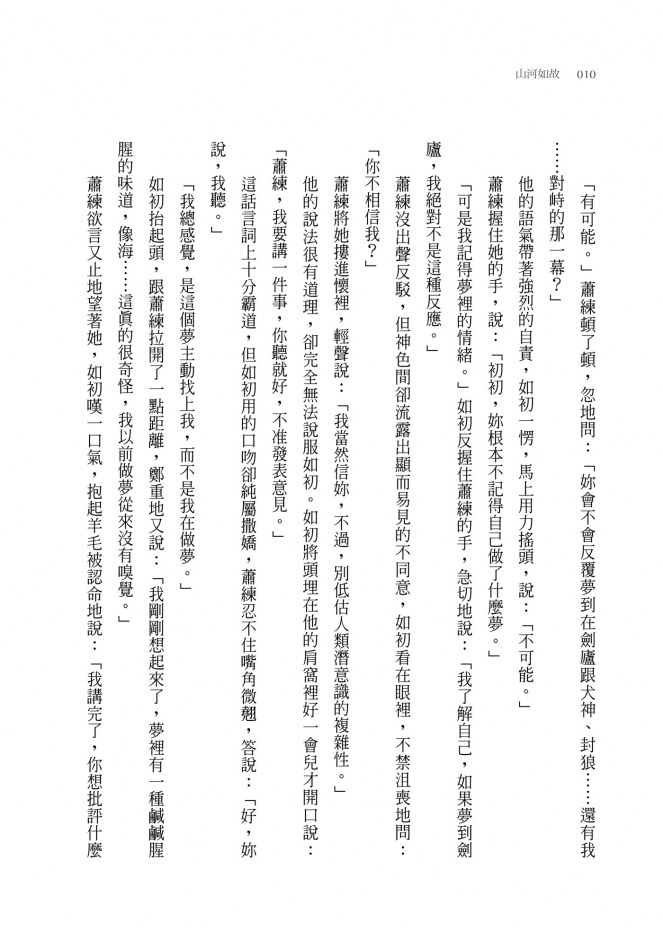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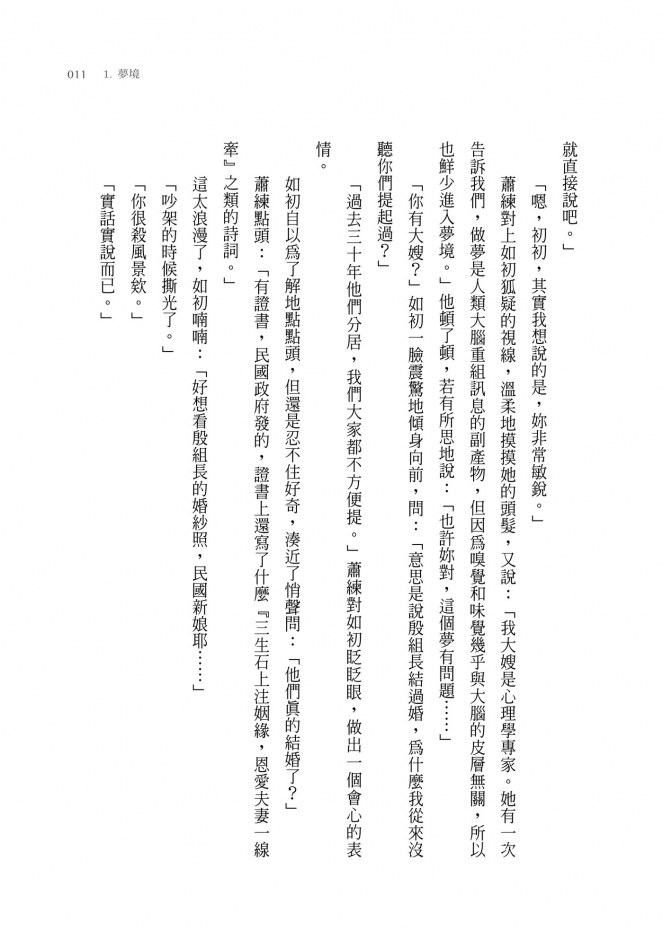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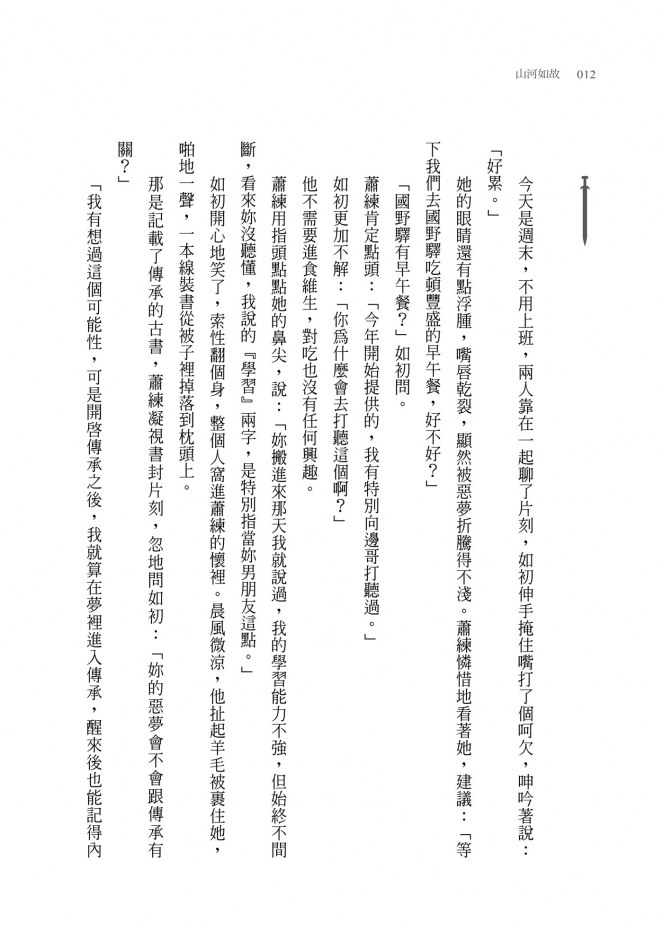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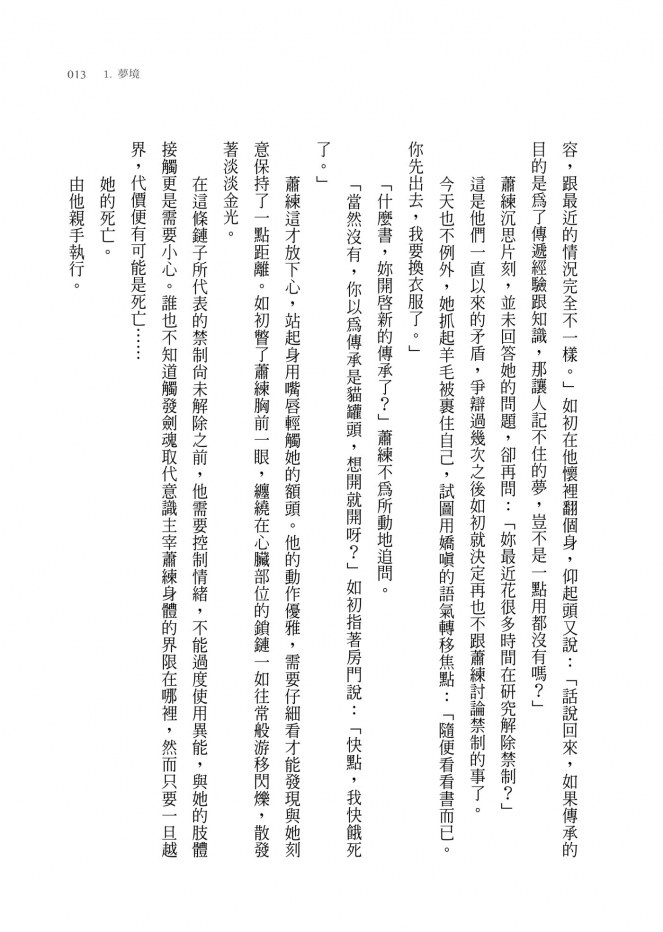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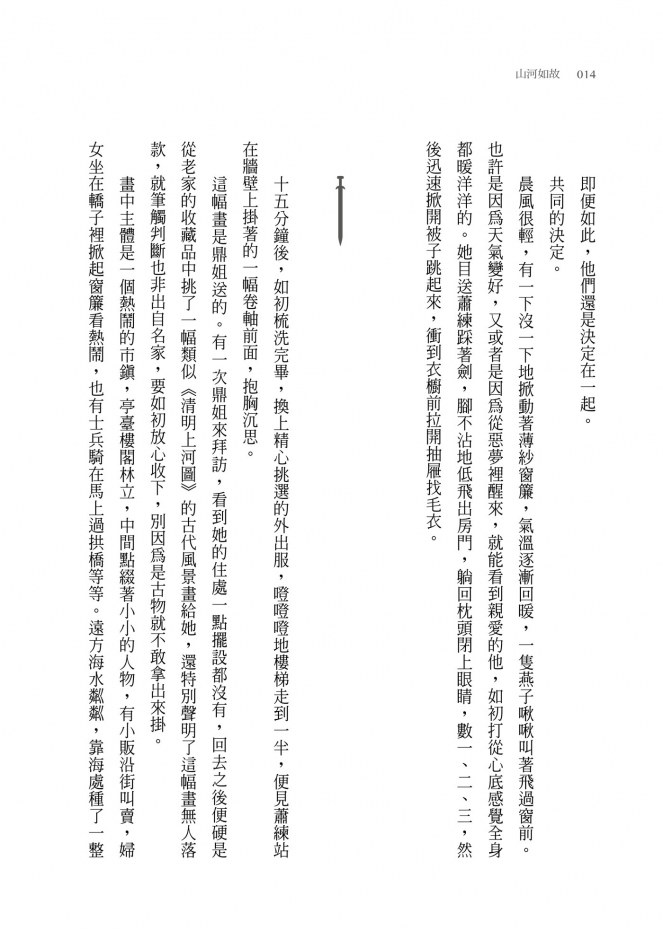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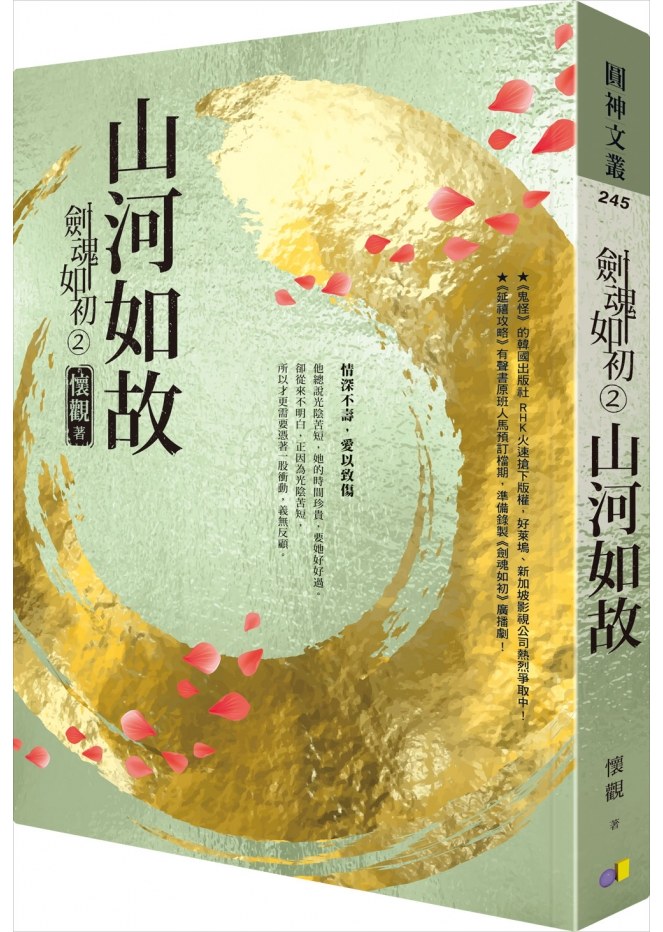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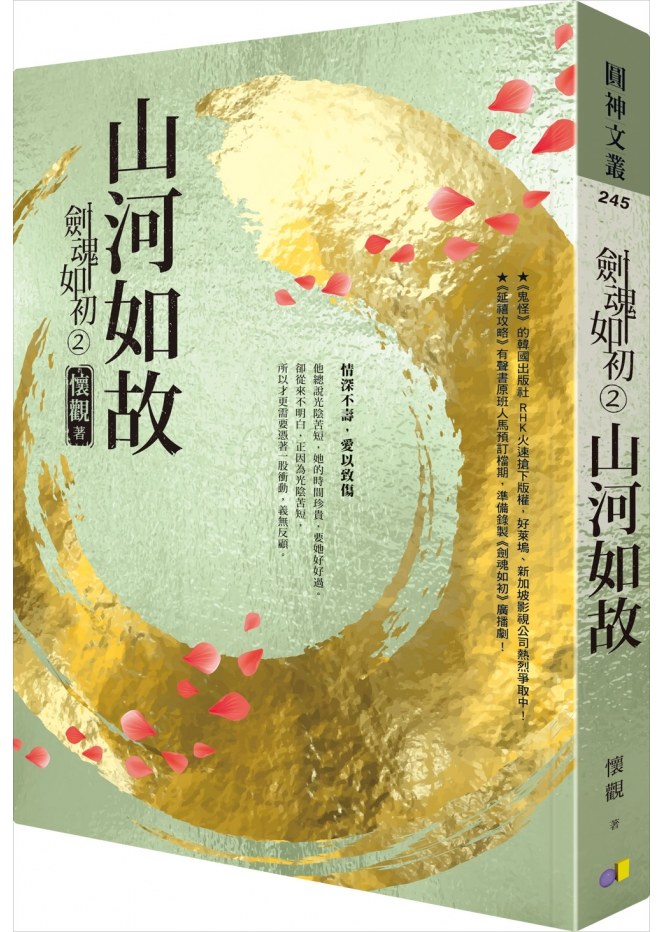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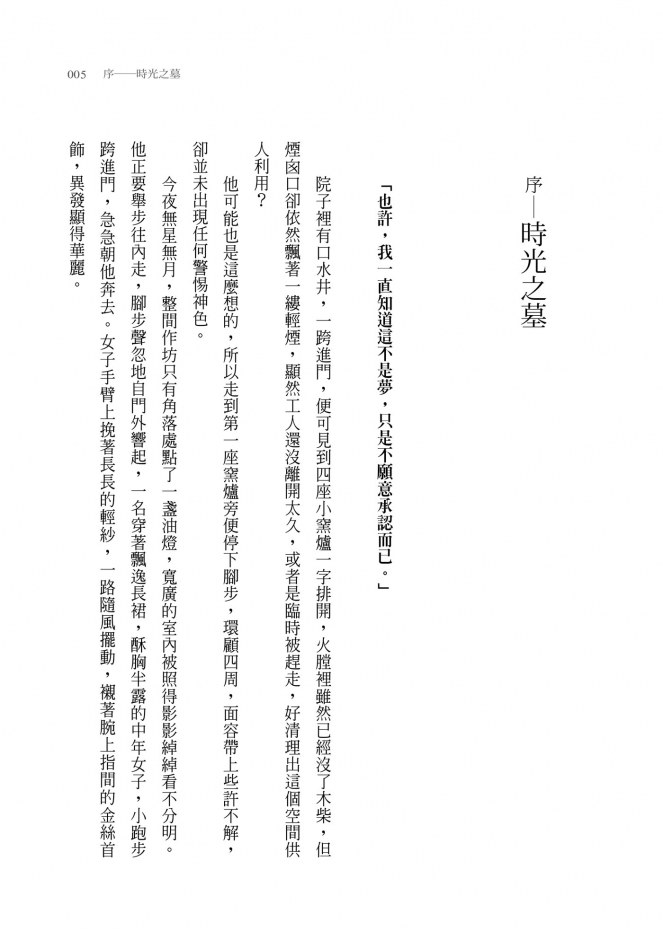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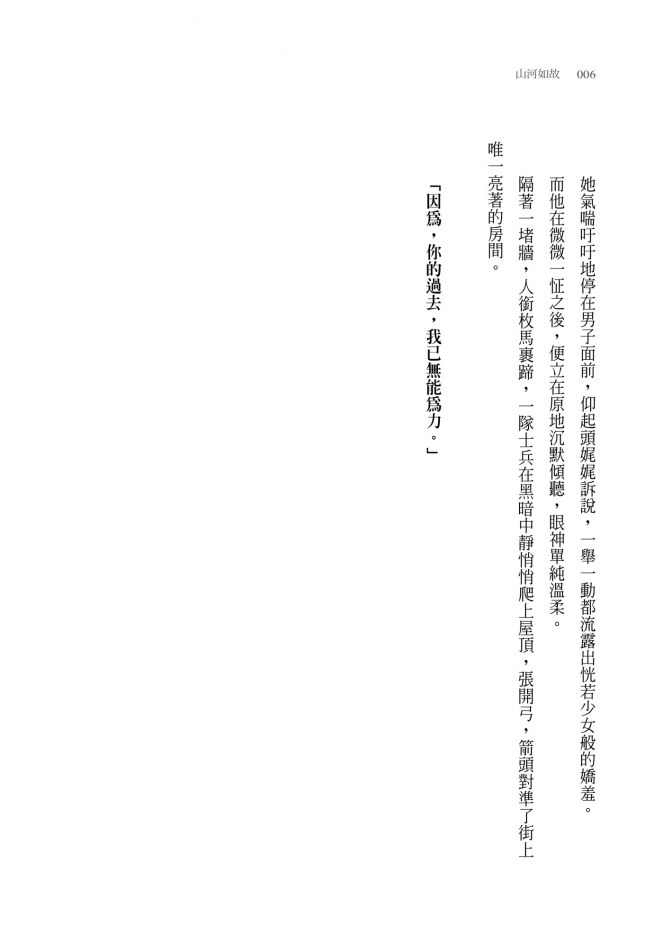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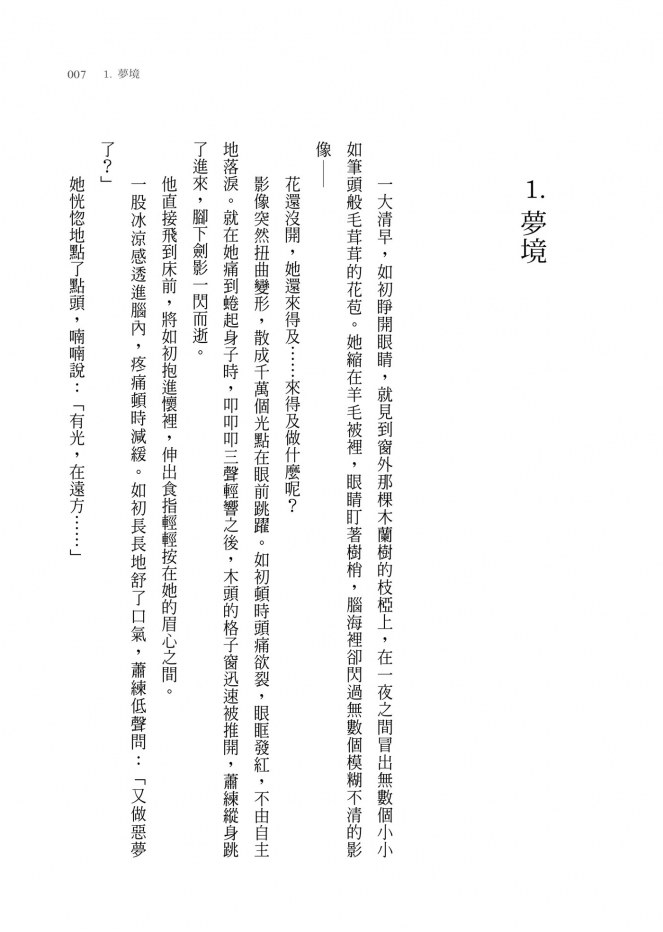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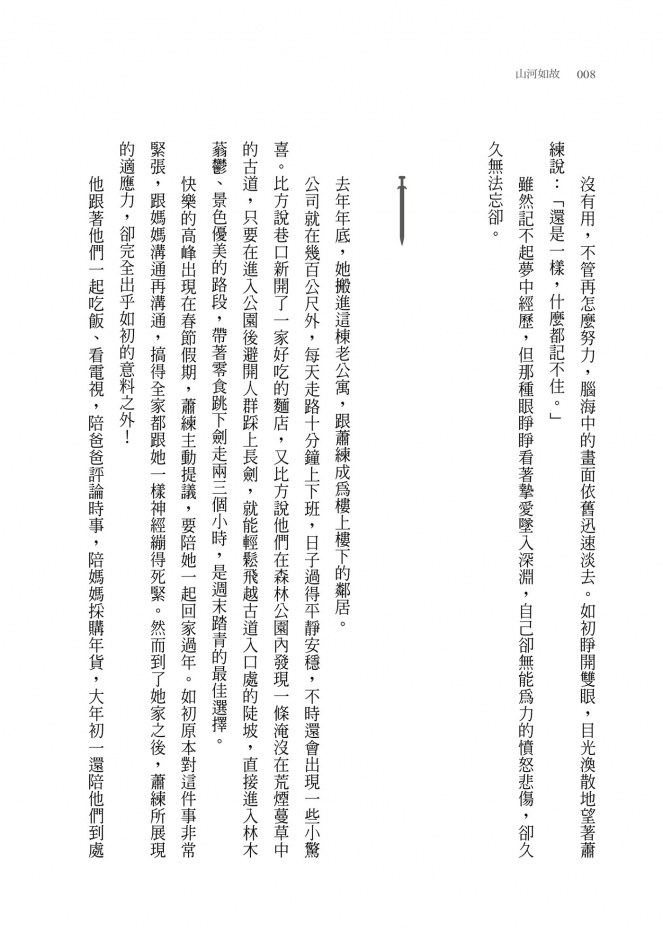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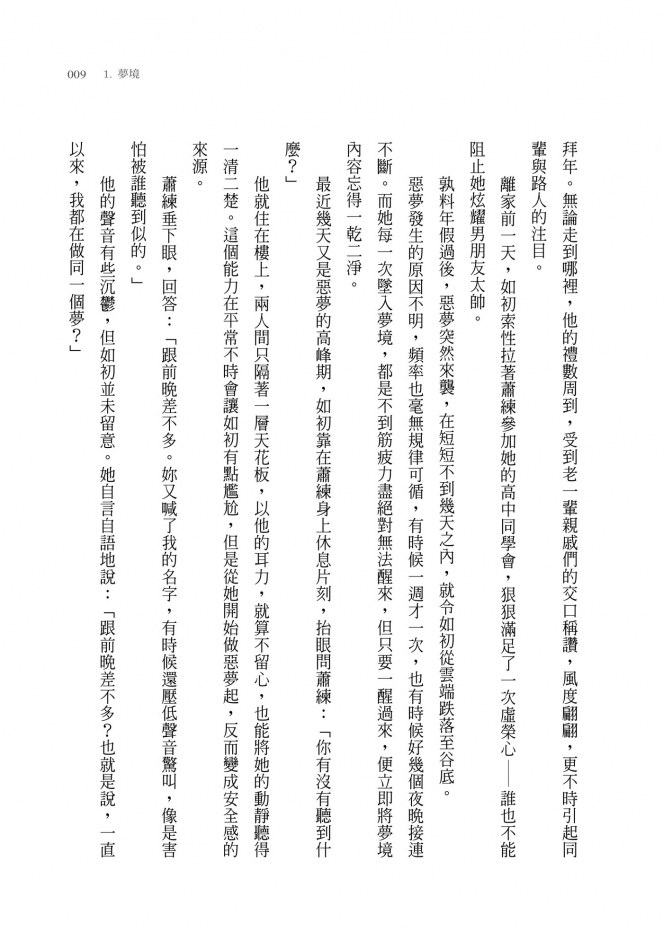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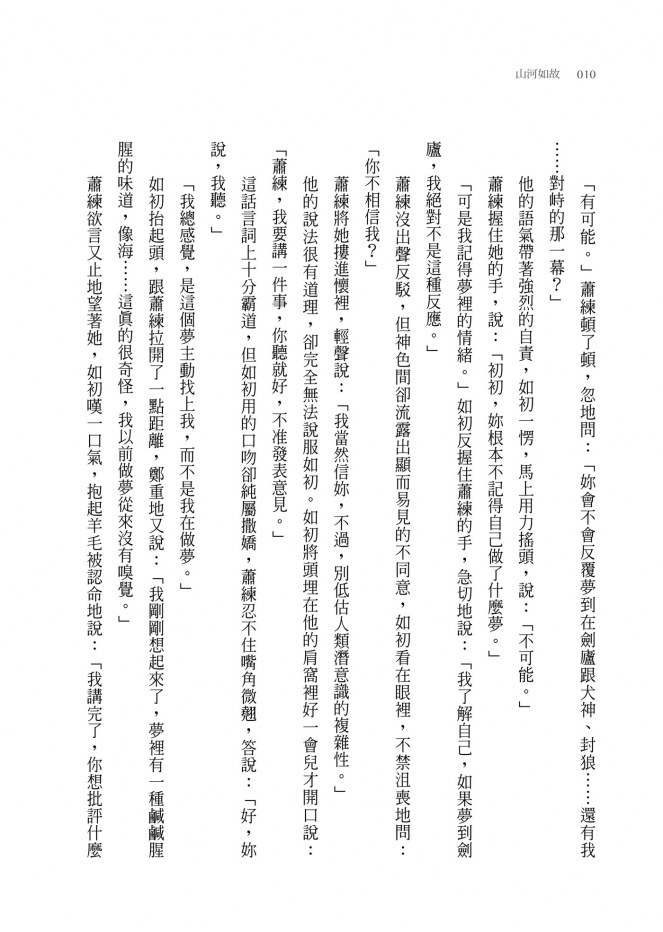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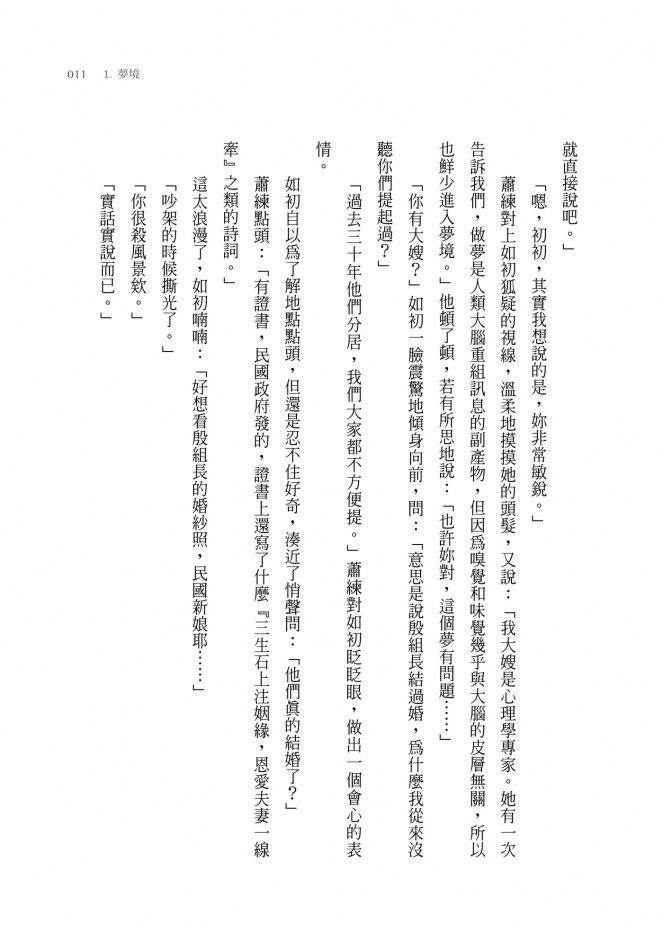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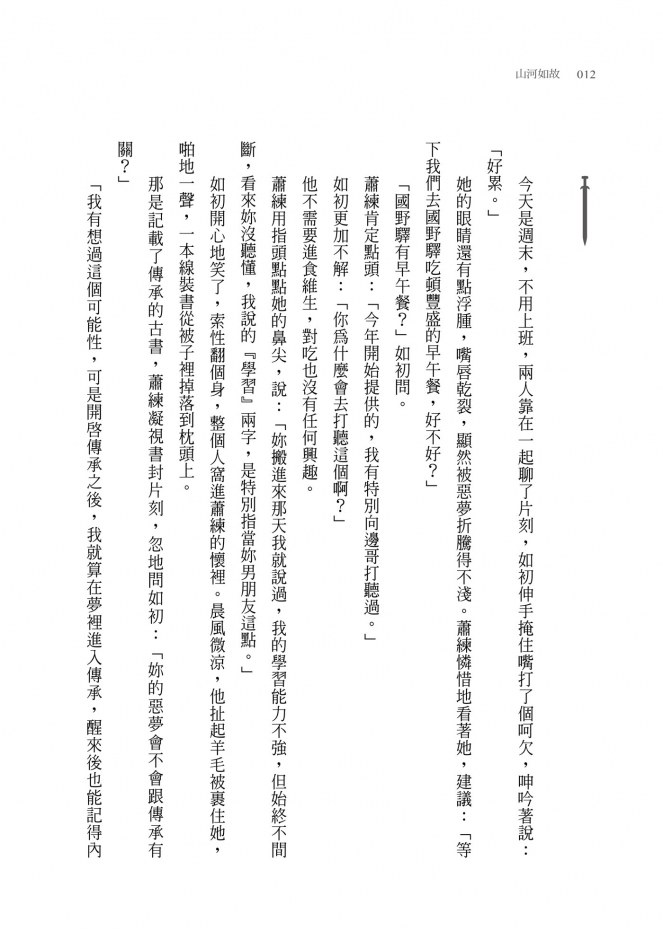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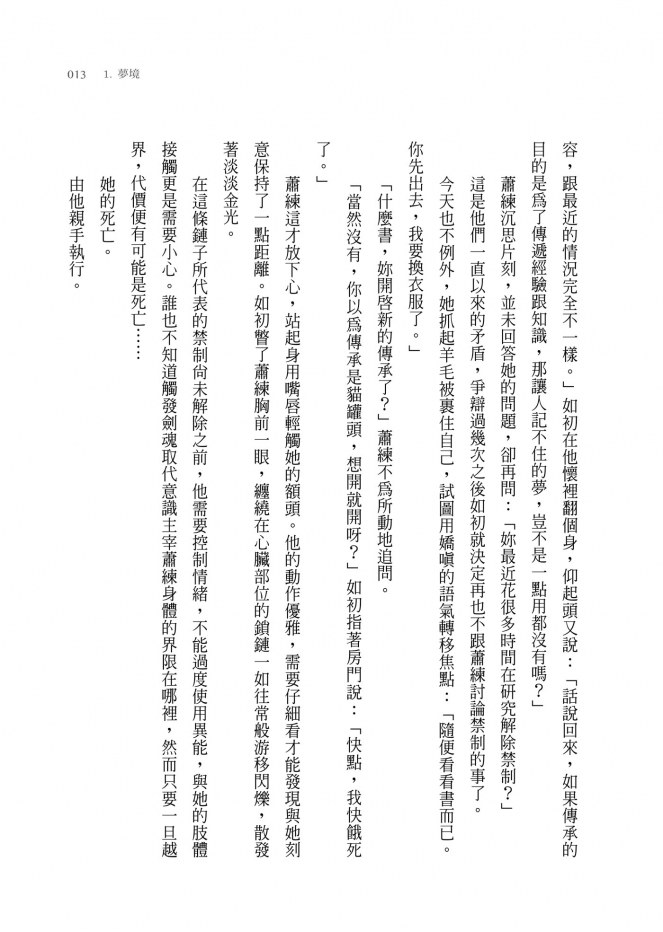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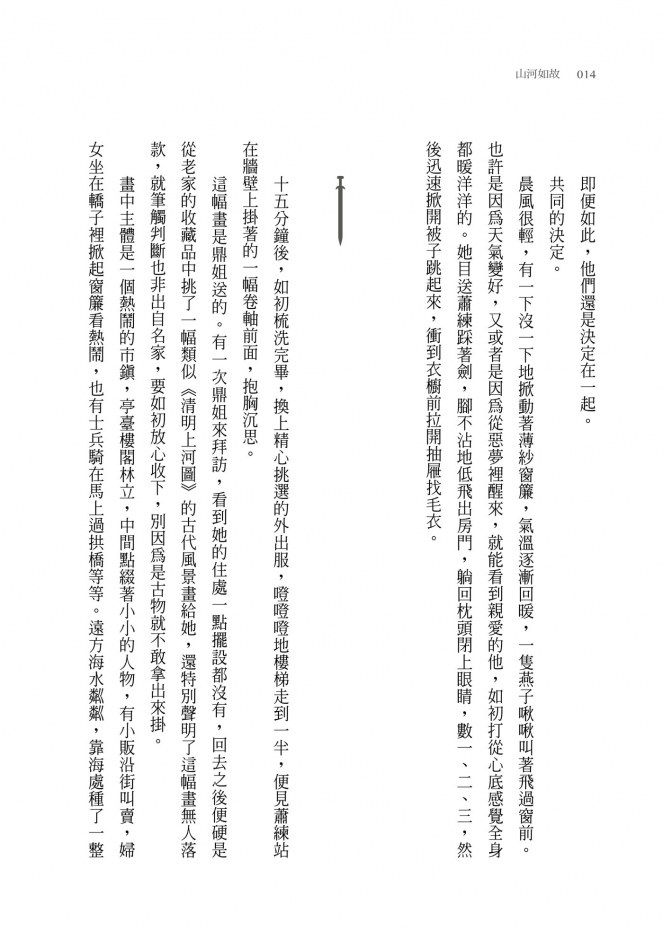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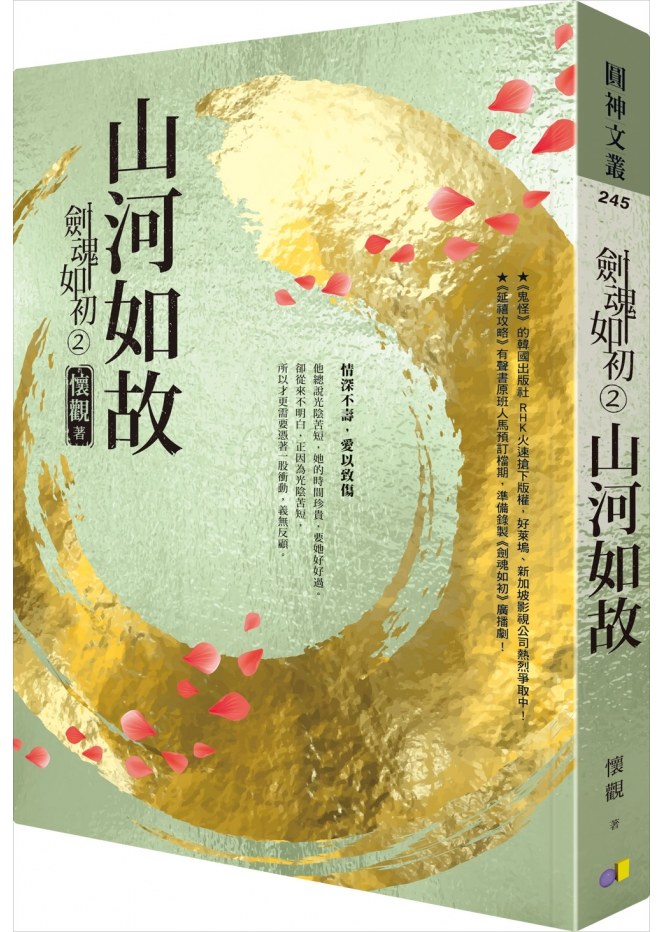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