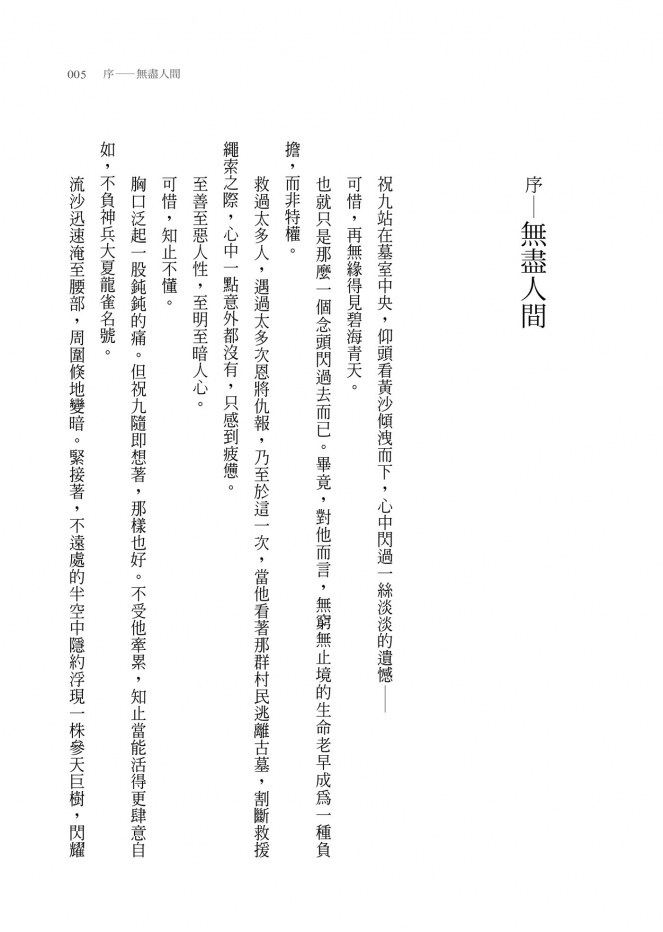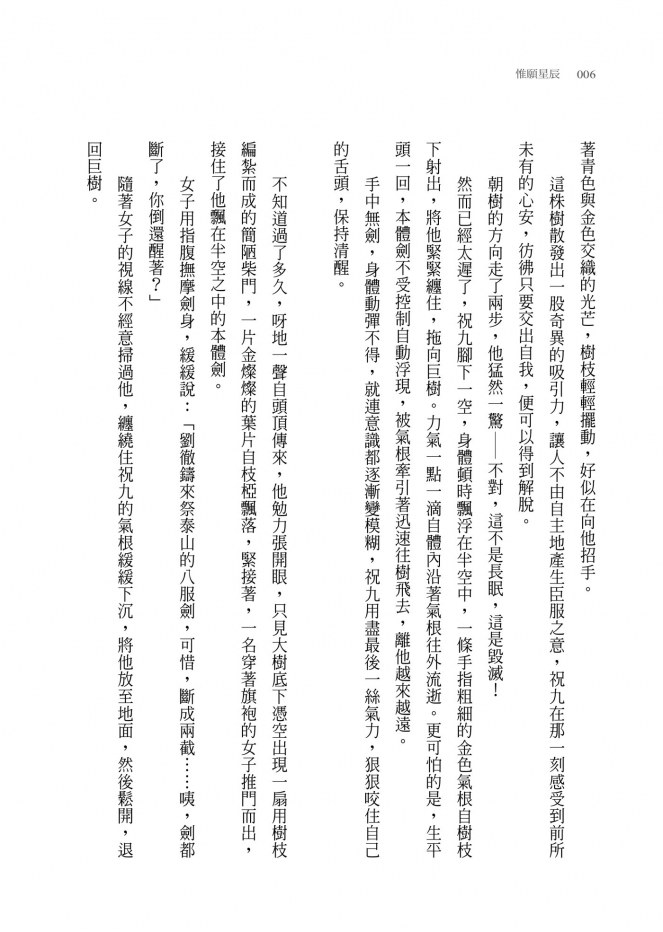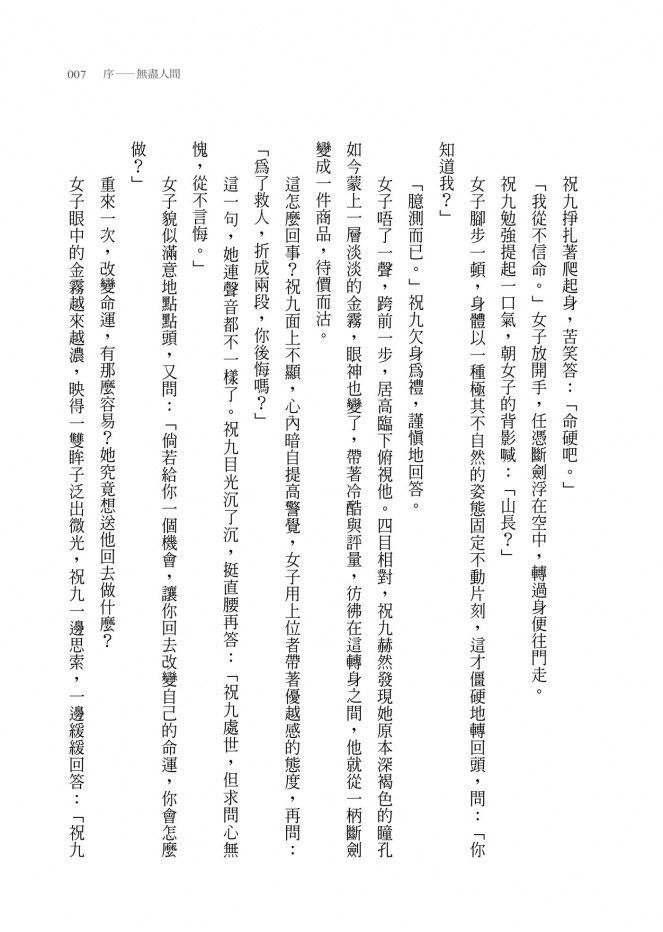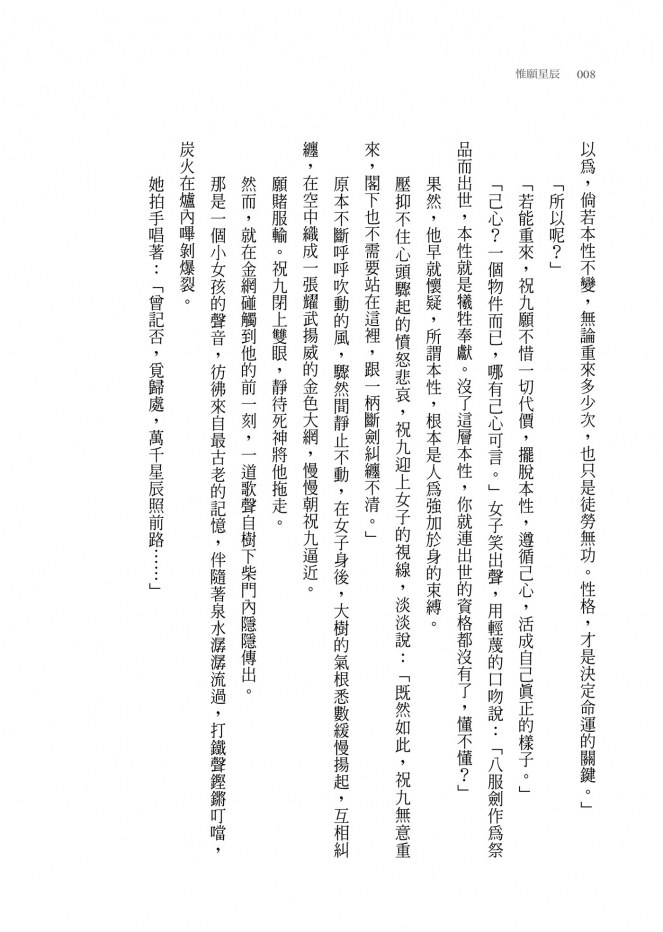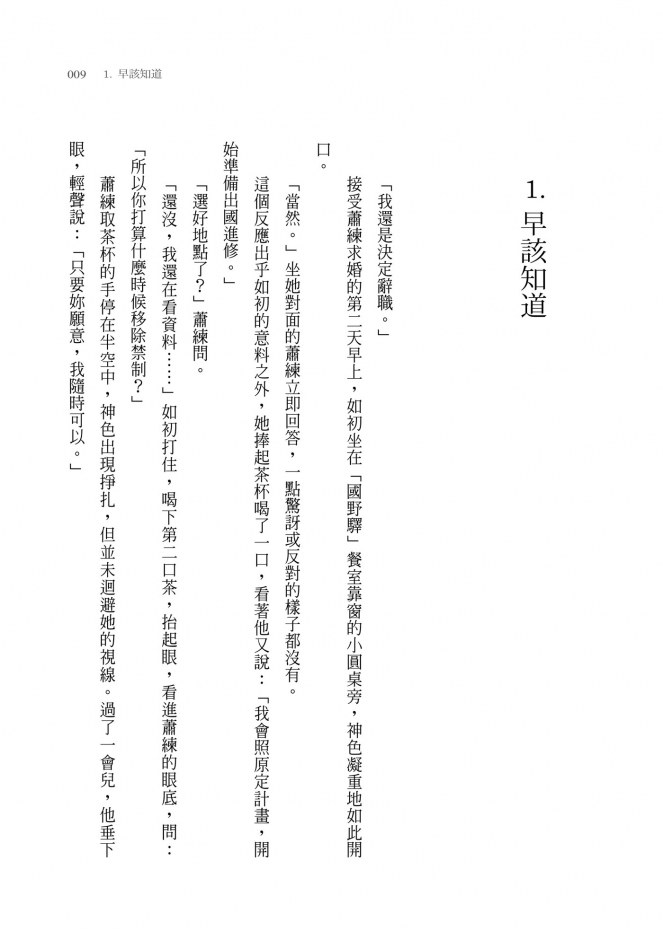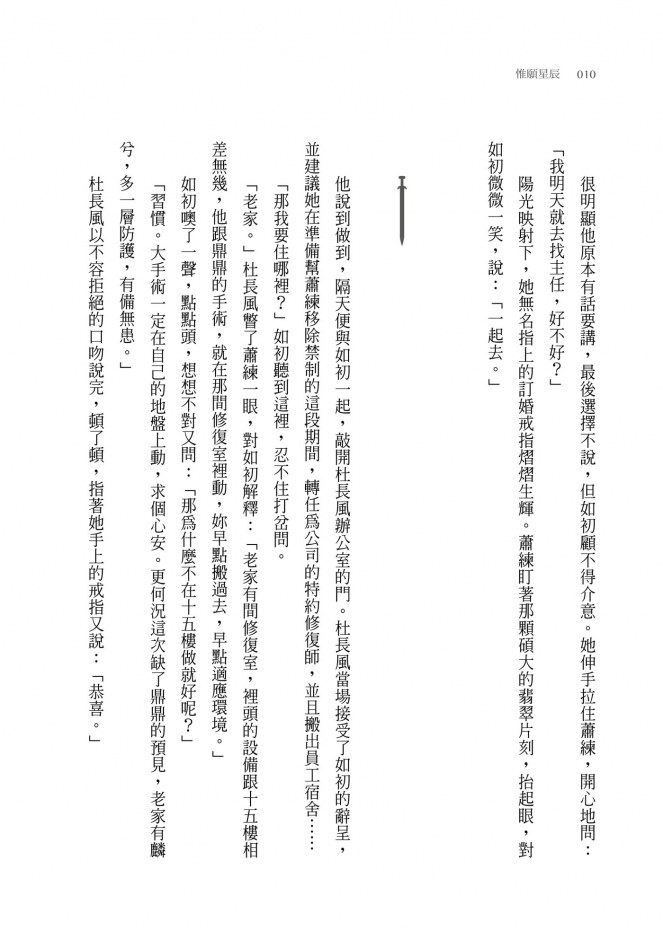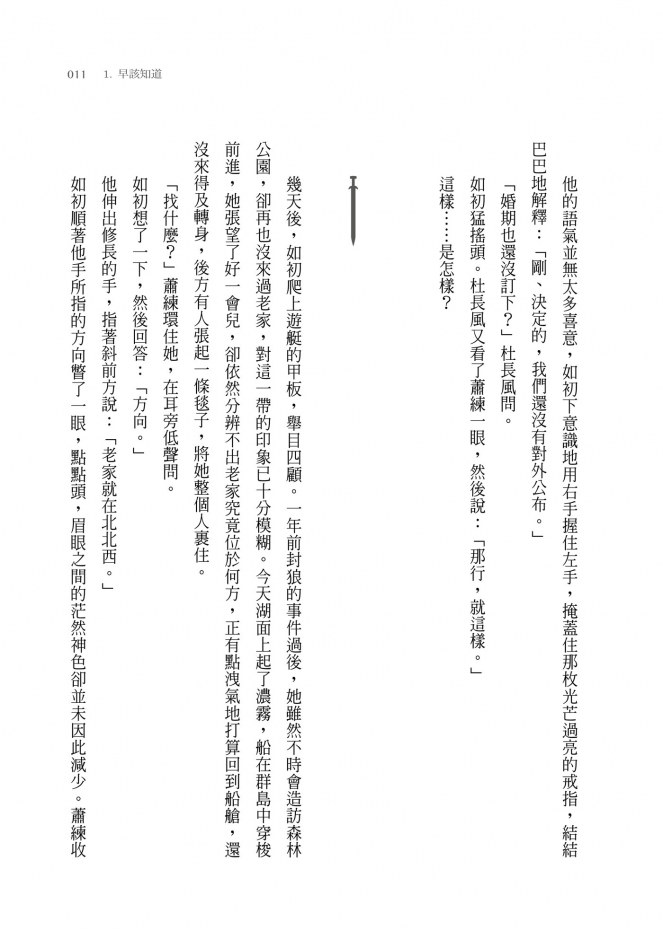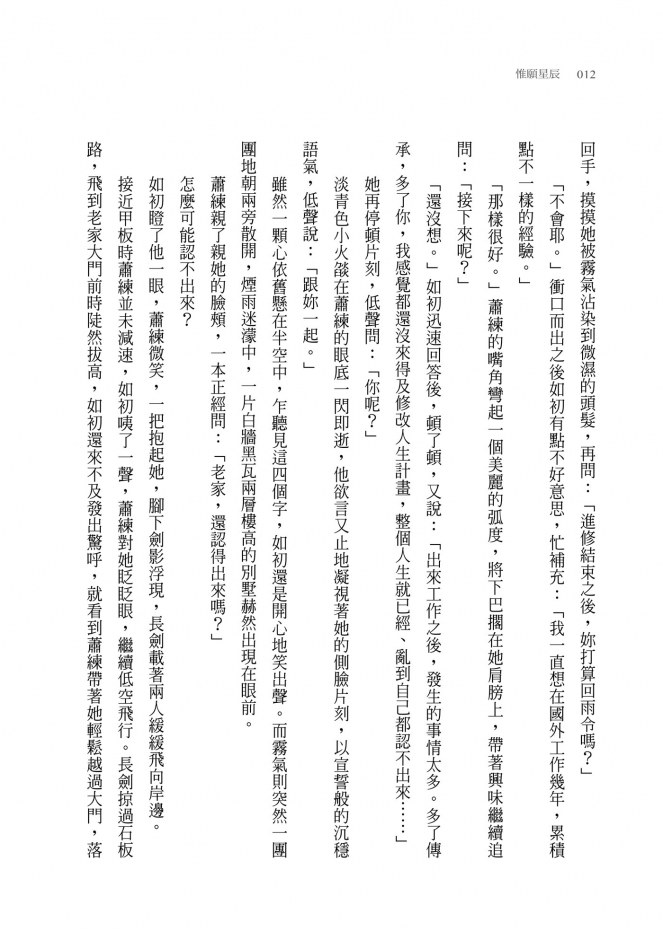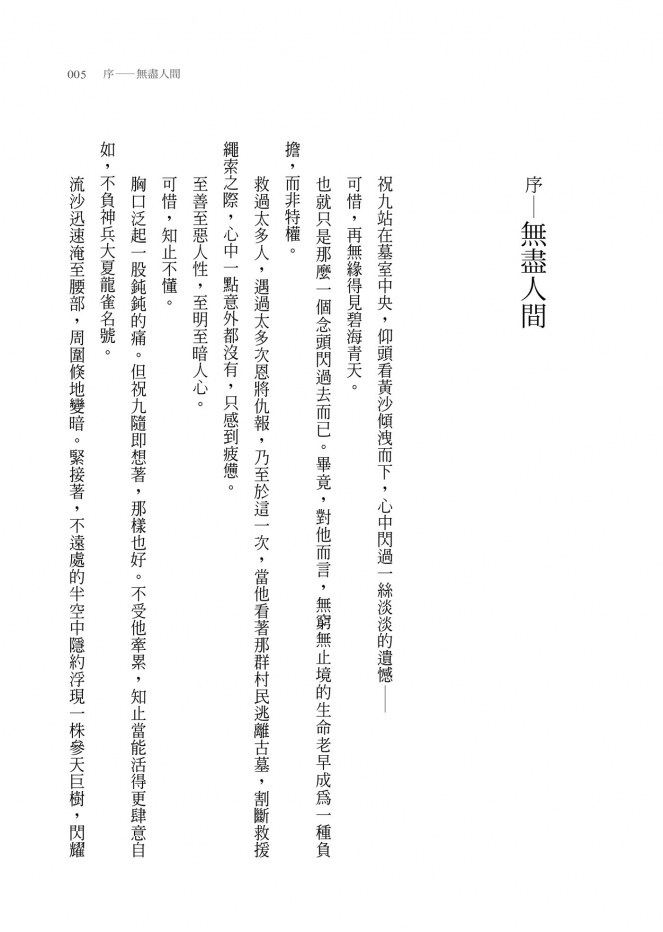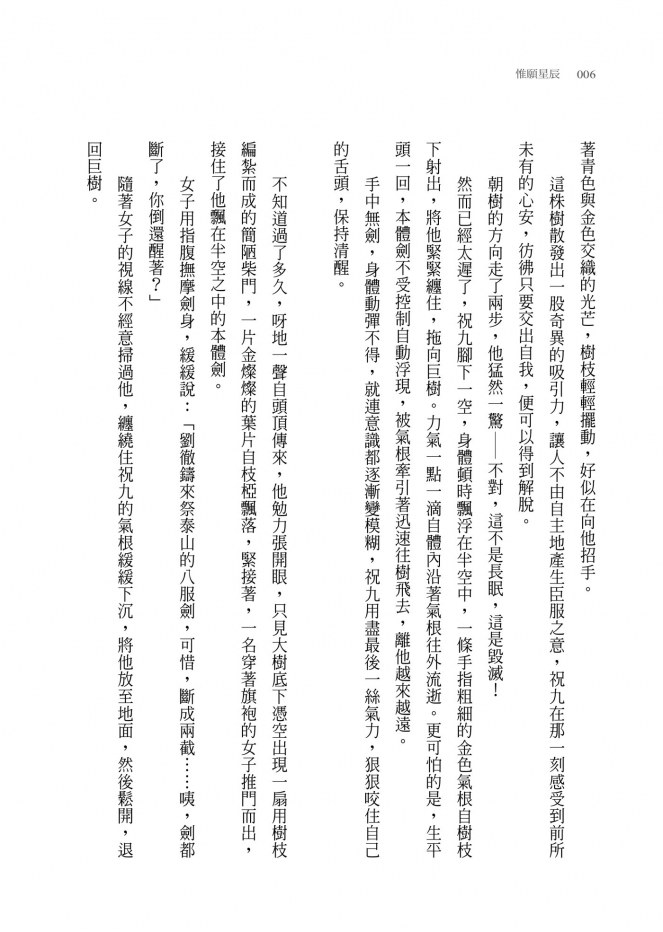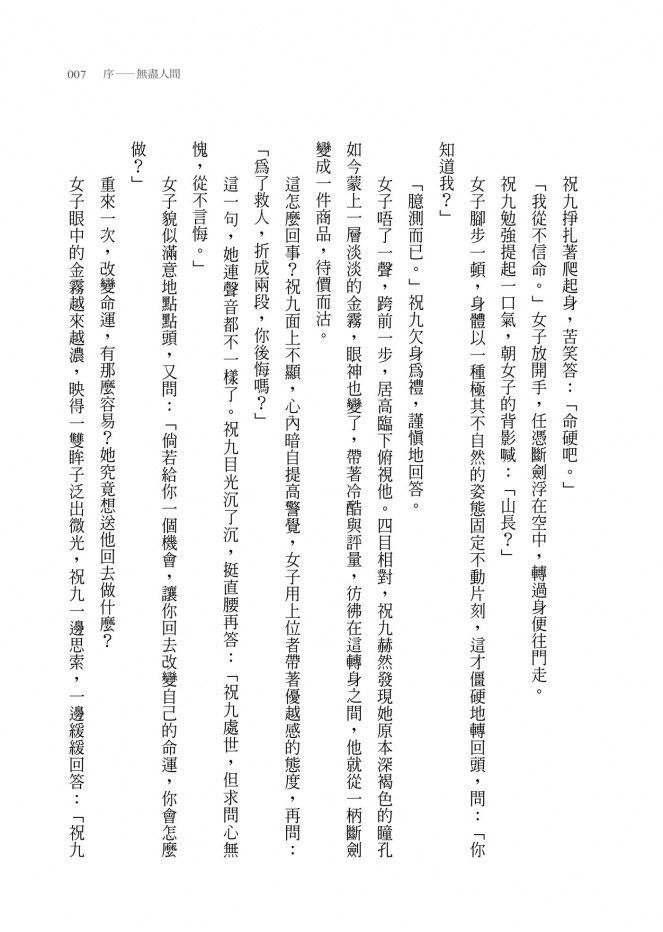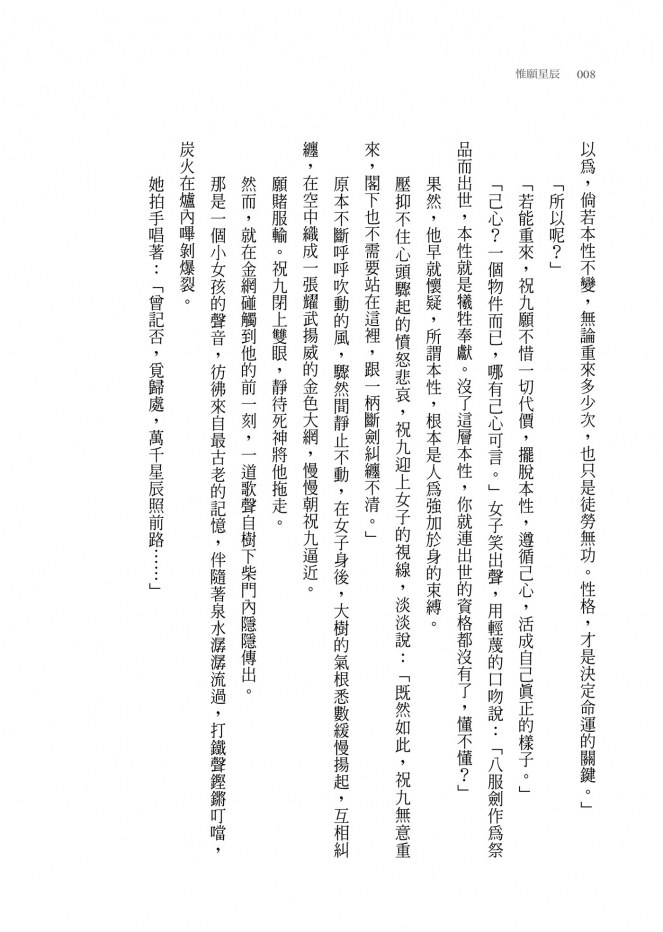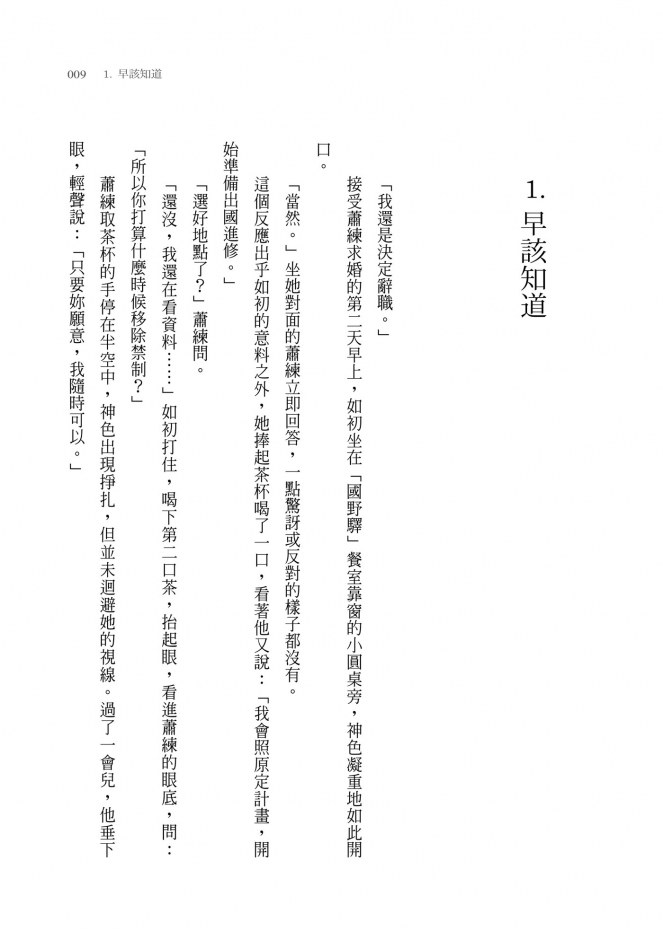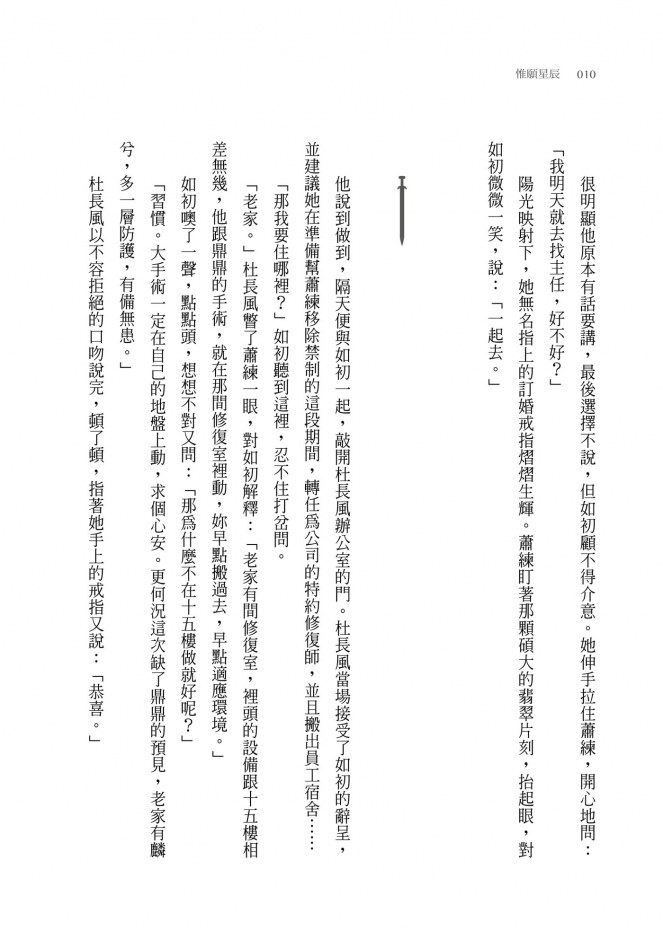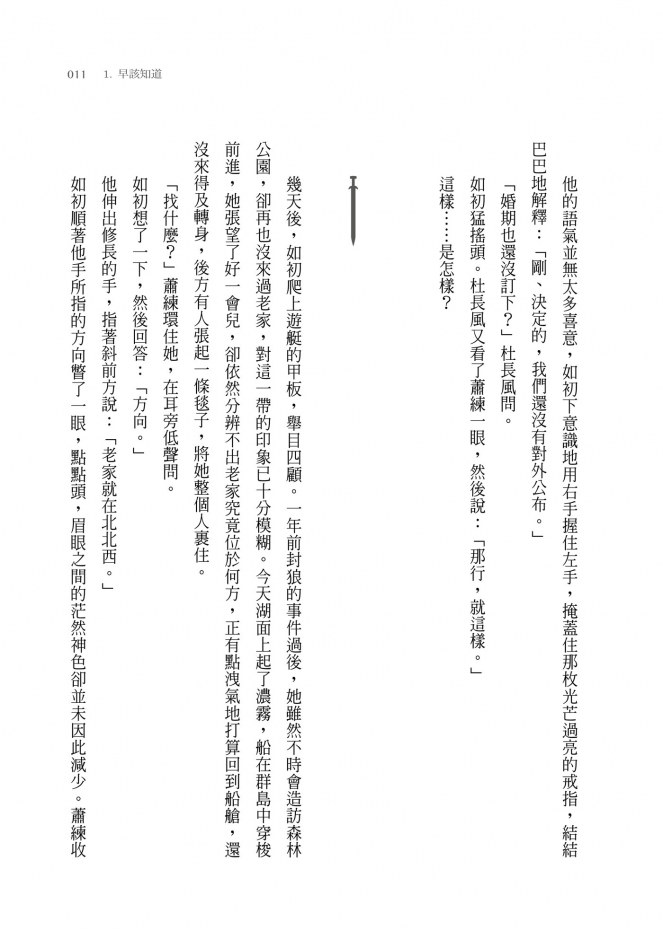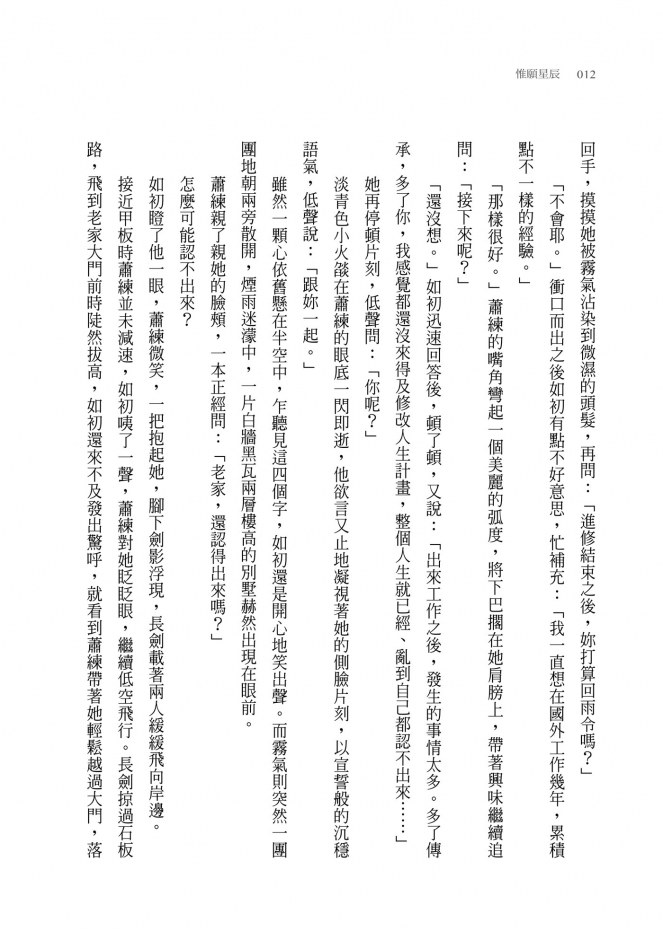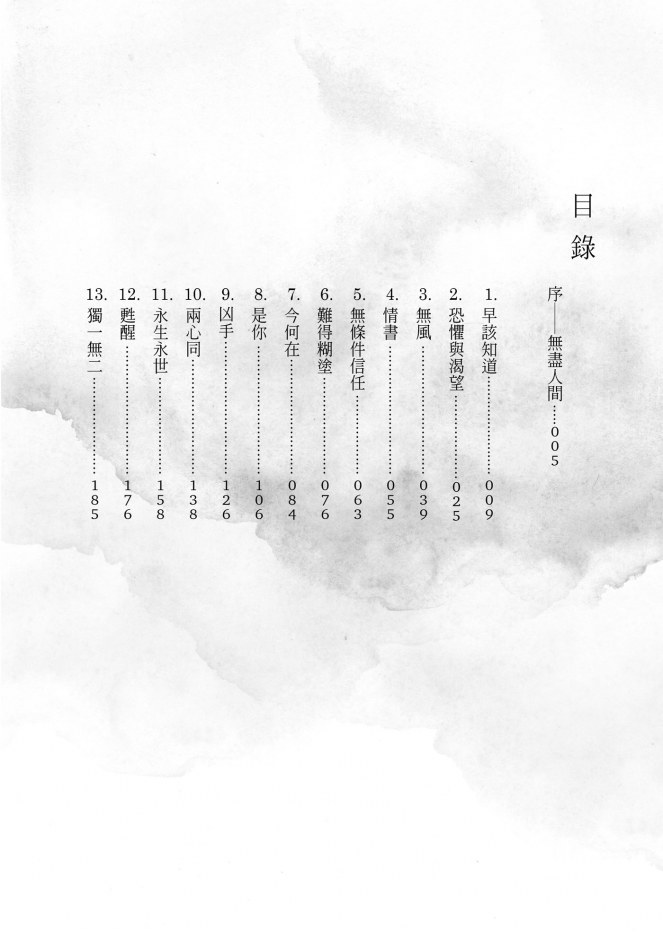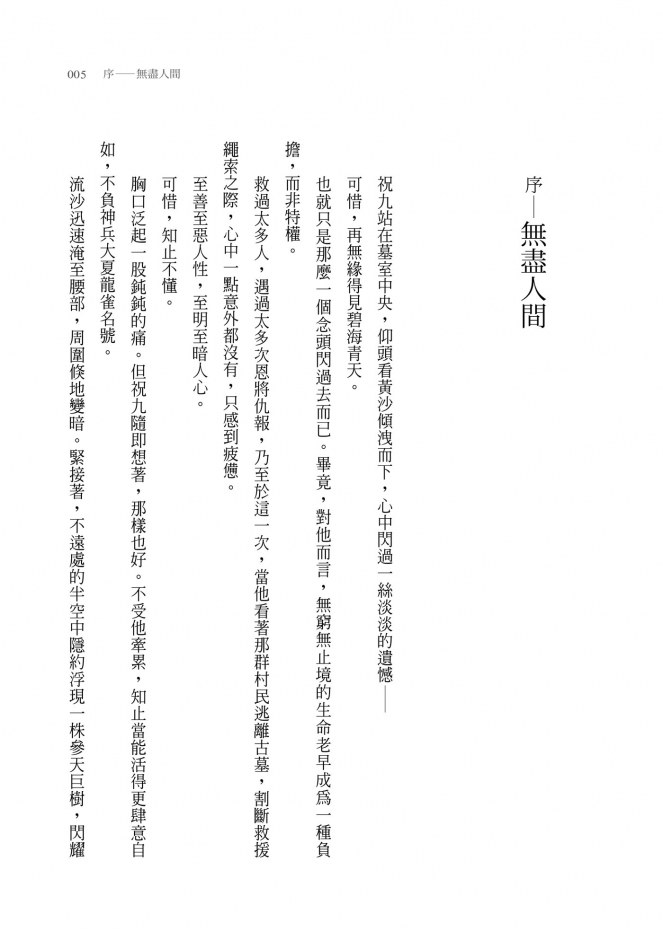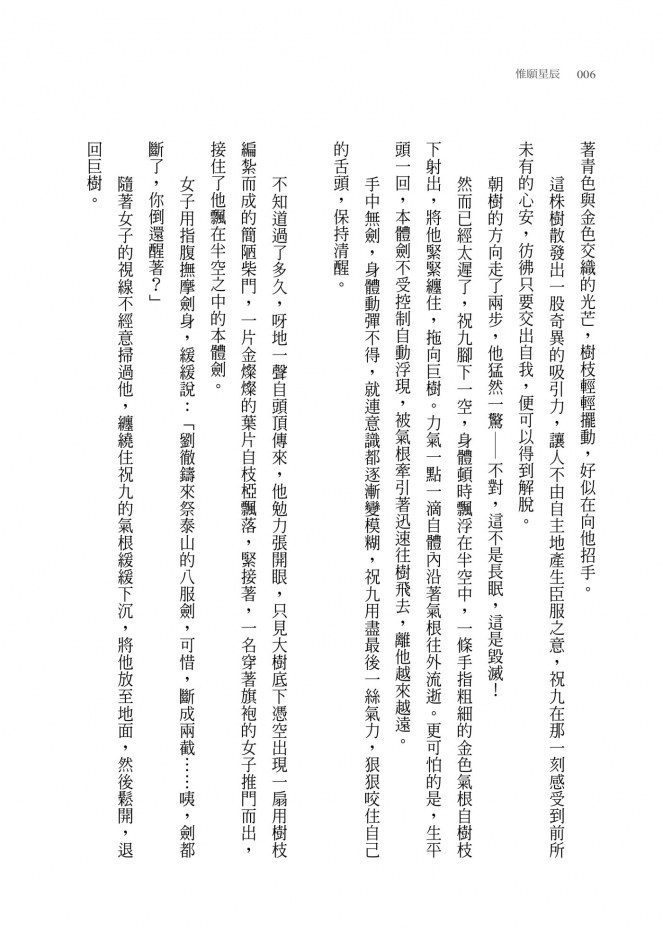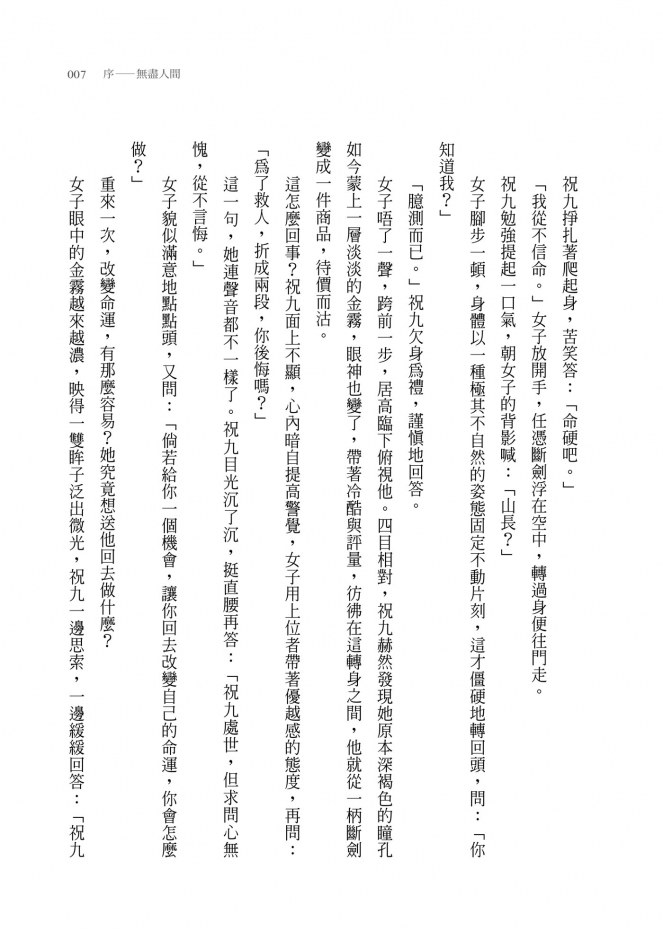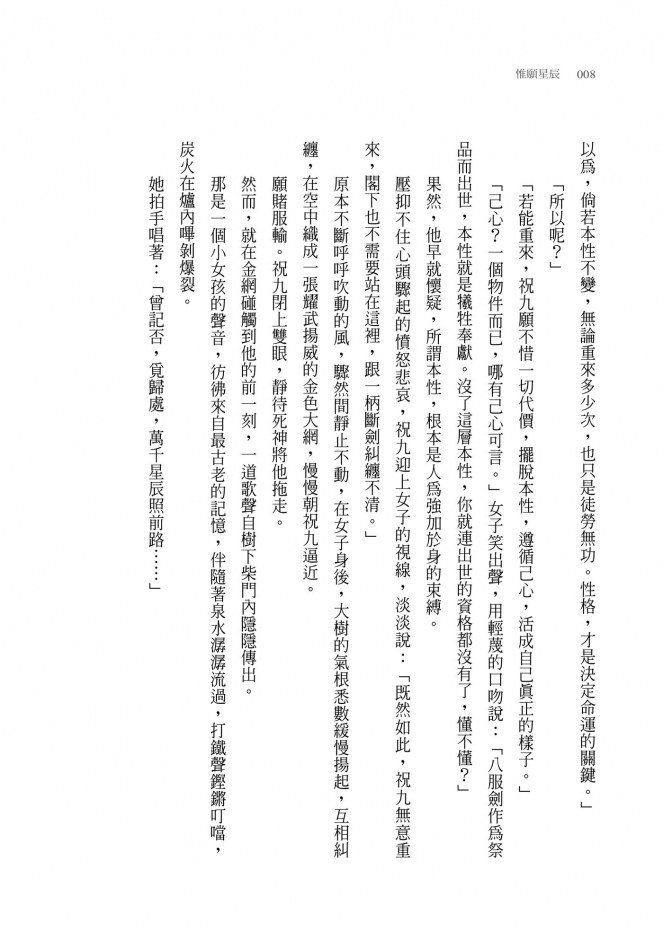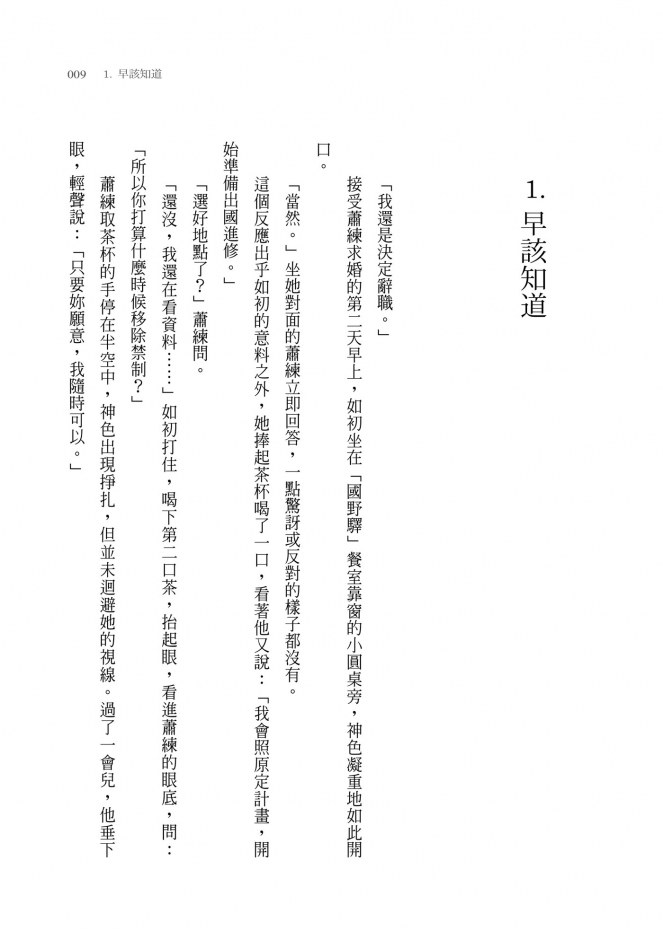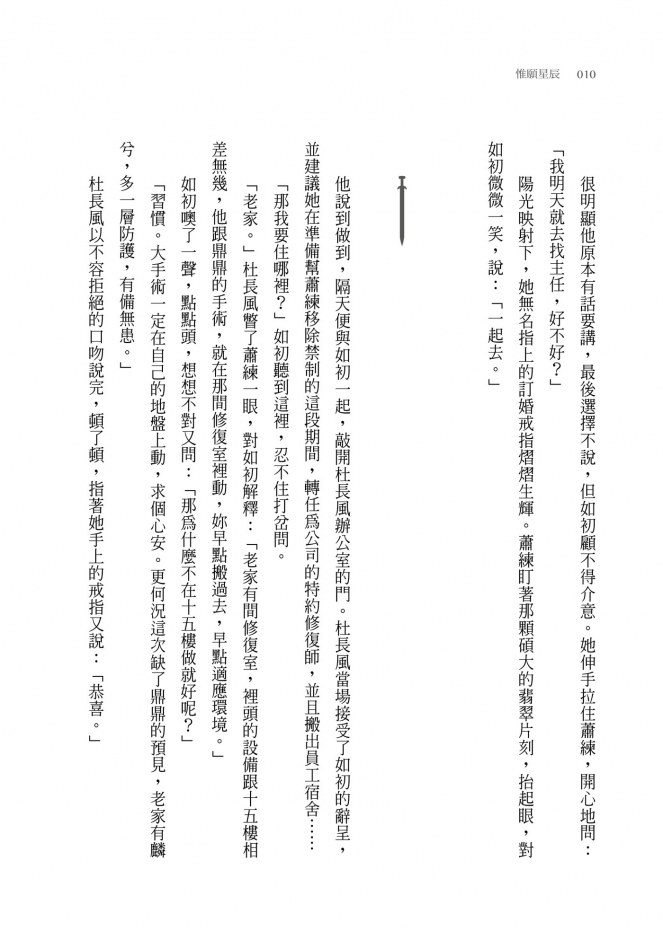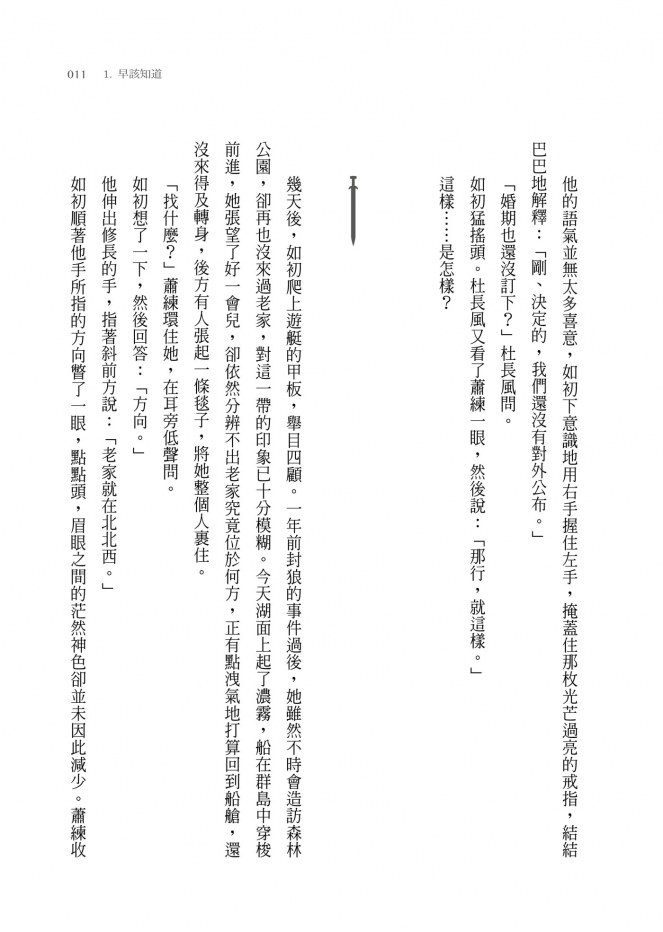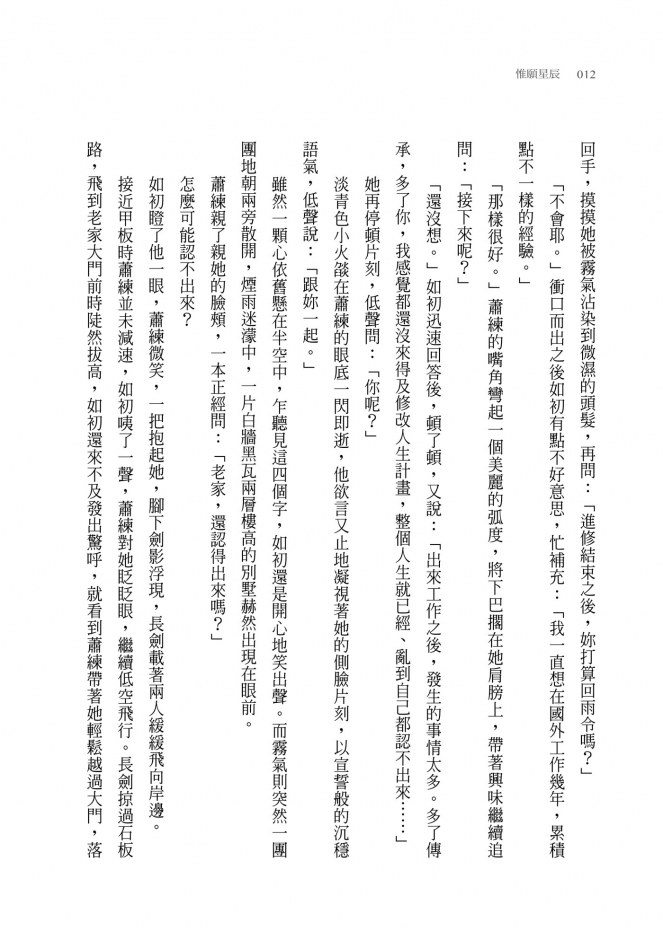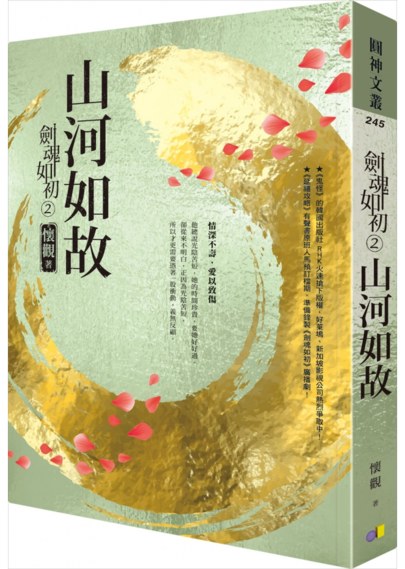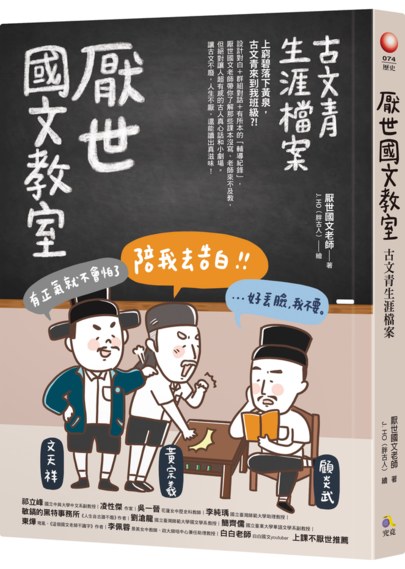1. 早該知道
「我還是決定辭職。」
接受蕭練求婚的第二天早上,如初坐在「國野驛」餐室靠窗的小圓桌旁,神色凝重地如此開口。
「當然。」坐她對面的蕭練立即回答,一點驚訝或反對的樣子都沒有。
這個反應出乎如初的意料之外,她捧起茶杯喝了一口,看著他又說:「我會照原定計畫,開始準備出國進修。」
「選好地點了?」蕭練問。
「還沒,我還在看資料……」如初打住,喝下第二口茶,抬起眼,看進蕭練的眼底,問:「所以你打算什麼時候移除禁制?」
蕭練取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中,神色出現掙扎,但並未迴避她的視線。過了一會兒,他垂下眼,輕聲說:「只要妳願意,我隨時可以。」
很明顯他原本有話要講,最後選擇不說,但如初顧不得介意。她伸手拉住蕭練,開心地問:「我明天就去找主任,好不好?」
陽光映射下,她無名指上的訂婚戒指熠熠生輝。蕭練盯著那顆碩大的翡翠片刻,抬起眼,對如初微微一笑,說:「一起去。」
他說到做到,隔天便與如初一起,敲開杜長風辦公室的門。杜長風當場接受了如初的辭呈,並建議她在準備幫蕭練移除禁制的這段期間,轉任為公司的特約修復師,並且搬出員工宿舍……
「那我要住哪裡?」如初聽到這裡,忍不住打岔問。
「老家。」杜長風瞥了蕭練一眼,對如初解釋:「老家有間修復室,裡頭的設備跟十五樓相差無幾,他跟鼎鼎的手術,就在那間修復室裡動,妳早點搬過去,早點適應環境。」
如初噢了一聲,點點頭,想想不對又問:「那為什麼不在十五樓做就好呢?」
「習慣。大手術一定在自己的地盤上動,求個心安。更何況這次缺了鼎鼎的預見,老家有麟兮,多一層防護,有備無患。」
杜長風以不容拒絕的口吻說完,頓了頓,指著她手上的戒指又說:「恭喜。」
他的語氣並無太多喜意,如初下意識地用右手握住左手,掩蓋住那枚光芒過亮的戒指,結結巴巴地解釋:「剛、決定的,我們還沒有對外公布。」
「婚期也還沒訂下?」杜長風問。
如初猛搖頭。杜長風又看了蕭練一眼,然後說:「那行,就這樣。」
這樣……是怎樣?
幾天後,如初爬上遊艇的甲板,舉目四顧。一年前封狼的事件過後,她雖然不時會造訪森林公園,卻再也沒來過老家,對這一帶的印象已十分模糊。今天湖面上起了濃霧,船在群島中穿梭前進,她張望了好一會兒,卻依然分辨不出老家究竟位於何方,正有點洩氣地打算回到船艙,還沒來得及轉身,後方有人張起一條毯子,將她整個人裹住。
「找什麼?」蕭練環住她,在耳旁低聲問。
如初想了一下,然後回答:「方向。」
他伸出修長的手,指著斜前方說:「老家就在北北西。」
如初順著他手所指的方向瞥了一眼,點點頭,眉眼之間的茫然神色卻並未因此減少。蕭練收回手,摸摸她被霧氣沾染到微濕的頭髮,再問:「進修結束之後,妳打算回雨令嗎?」
「不會耶。」衝口而出之後如初有點不好意思,忙補充:「我一直想在國外工作幾年,累積點不一樣的經驗。」
「那樣很好。」蕭練的嘴角彎起一個美麗的弧度,將下巴擱在她肩膀上,帶著興味繼續追問:「接下來呢?」
「還沒想。」如初迅速回答後,頓了頓,又說:「出來工作之後,發生的事情太多。多了傳承,多了你,我感覺都還沒來得及修改人生計畫,整個人生就已經、亂到自己都認不出來……」
她再停頓片刻,低聲問:「你呢?」
淡青色小火燄在蕭練的眼底一閃即逝,他欲言又止地凝視著她的側臉片刻,以宣誓般的沉穩語氣,低聲說:「跟妳一起。」
雖然一顆心依舊懸在半空中,乍聽見這四個字,如初還是開心地笑出聲。而霧氣則突然一團團地朝兩旁散開,煙雨迷濛中,一片白牆黑瓦兩層樓高的別墅赫然出現在眼前。
蕭練親了親她的臉頰,一本正經問:「老家,還認得出來嗎?」
怎麼可能認不出來?
如初瞪了他一眼,蕭練微笑,一把抱起她,腳下劍影浮現,長劍載著兩人緩緩飛向岸邊。
接近甲板時蕭練並未減速,如初咦了一聲,蕭練對她眨眨眼,繼續低空飛行。長劍掠過石板路,飛到老家大門前時陡然拔高,如初還來不及發出驚呼,就看到蕭練帶著她輕鬆越過大門,落到庭院裡。
緊接著,他抱著她一路穿過放置本體的大廳,掛有名家真跡的寬廣起居室,拐個彎順著樓梯飛上二樓,行經一條長長的整面落地玻璃窗走廊之後,才將她放在一扇房門前面。
「妳的房間。」他對她這麼說。
如初推開房門,看到一間十分雅致的套房。空間很大,家具雖只有一桌一椅跟一張床,但每件都是精品,擺設得錯落有致,十分具有藝術感。
然而不知道為什麼,如初有點麻木了,她隨意打量環境一眼,忽地想起來,忙問蕭練:「鼎姐以前布置的?」
他點頭,如初低頭看著幾乎要淹沒腳背的長毛地毯,喃喃說:「喬巴會愛死這塊地毯……」
「妳漏了一個重點。」蕭練指指地毯:「我住樓下。」
於是,他們再度成為樓上樓下的鄰居。然而體重已經超過五公斤的黃貓喬巴,卻並未如如初所料地愛上地毯,牠在搬進老家的第二天,便溜出房門,找到一條如初始終沒搞清楚的祕密通道,足足失蹤了大半天。如初嚇得發動全家幫忙找貓,最後還是靠站在屋頂上的青銅麒麟一聲長嘶,大家這才注意到,喬巴正悠閒地躺在屋頂晒太陽。
搬進老家之後,如初還是照以往上班的節奏,每天規律進出位於一樓的修復室,針對專案計畫繼續進行研究。
在這間嶄新的修復室裡,她總共需要完成兩項專案——第一項是跟秦老師一起,修復鼎姐鏽蝕的右耳;第二項則是獨立作業,解除蕭練的禁制。
幾天後,秦觀潮也搭船來到老家。他板著臉、背著雙手在新修復室裡轉了兩圈,走到每個會用上的儀器前面檢查一遍,便又板著臉離開,從頭到尾都對如初愛理不理,讓有心想跟老師多聊幾句的她碰了一鼻子灰。
雖然如此,是夜,如初還是忍不住走進起居室,走到正敲打鍵盤的殷含光面前,問:「現在還來不來得及改變計畫,邀老師加入?」
「我以為,早在去年妳瞞著他私下打造禁制的時候,就已經將他排除在外了。」含光眼睛盯著電腦螢幕,頭也不抬地如此回答。
他最近說話口氣很衝,但如初可以理解。隨著表定移除禁制的時間一天天逼近,她的心情也越來越緊繃,一點風吹草動都能讓她跳起來。將心比心,想來含光也不好受。
她按下心裡的不舒坦,又對含光說:「之前我打造禁制,無論成功或失敗,對蕭練都沒影響。這次不一樣,還是請老師也加入吧?」
含光抬起頭,冷冷地瞧著她問:「如果修復現場妳出了任何狀況,秦觀潮能接手嗎?」
當然不行。如初搖頭,含光又問:「那邀他進場目的何在?」
「總是,多一個人幫忙——」
「之前我就告訴過妳,凡是關於我們本體的修復工作,涉及的人員越少越好。」含光打斷她,用銳利目光盯住她,又說:「如果妳要一個助手幫忙遞工具或清潔檯面,那儘管訓練我或承影都行,妳需要嗎?」
早在去年底,如初便已將移除禁制的流程寫下,連同辭呈一起交給杜主任。過去半個多月,她又將流程反覆檢討改進,到如今已熟到閉著眼睛都能動手的地步。說實話,這種情況下多一個人在修復室,根本是徒增干擾。
所以究竟為什麼,她會需要秦觀潮進場?
她只是害怕,怕在關鍵時刻,獨自承擔。
如初深深吸了口氣,對上含光的視線,答:「不用。」
「別理大哥,會怕才正常。」原本坐在起居室另一端的承影站起身,雙手插在口袋裡走了過來,一派輕鬆地說:「不過妳也別緊張,反正老三過去百年來活得超廢,不成功大不了保持原狀……」
此時蕭練正好走進來,聞言揚起雙眉,承影微笑,面不改色繼續往下講:「我的意思是,過去一百年,老三韜光養晦,把日子過得像隻烏龜,挺好。」
當然如初聽得出來承影在搞笑,但她笑不出來,只胡亂點點頭,拉住蕭練的衣袖,問:「我移除禁制的時候,你會失去意識吧?」
「當然。」他對她一笑,又說:「這樣反而方便,妳放手做,沒有牽掛。」
他近來彷彿想通了什麼,舉手投足多了三分灑脫,眉目間不再如往常般沉鬱,這個笑容再加上無與倫比的精緻容顏,能教人頓時淪陷其中,再也挪不開眼。
如初非常希望自己能夠淪陷,只可惜事與願違。她怔怔地看著他的臉,心一點一點往下沉,再問:「那劍魂呢?如果過程出了任何意外,即使你失去意識,劍魂也一定會現身保護本體的,對不對?」
蕭練默不作聲,含光取下眼鏡揉了揉眉心,不耐煩地答:「從崔氏那次經驗判斷,顯然不對,我們對傳承的了解還是太少……」
說到這裡,含光猛地打住,然而承影注意到他的異樣,看向含光的目光微沉,眼神滿是疑惑。如初則倒抽一口冷氣,將蕭練抓得更緊些,喃喃地說:「我們從來沒有評估過移除禁制失敗的話,你會、你會變成怎麼樣……」
「不需要評估。不會失敗。」蕭練沉聲如此答。
他的聲音充滿自信,如初幾乎要被說服了,她小聲問:「真的嗎?」
「這世上沒有百分之百。」含光插嘴。
蕭練與承影同時瞪了含光一眼,含光不為所動,承影拍拍如初的肩膀,說:「沒事,手術前半小時,麟兮會打開防護罩,確保手術過程不受外界干擾。說到底,當天妳的臨場表現才最要緊,妳出任何差錯,我們都只能站在外面乾瞪眼。」
掌心開始冒汗,如初點頭,喃喃答:「我會盡力——」
「盡力不夠,」含光打斷她,冷冷說:「需要百分之百,不然——」
「你剛剛才說這世上沒有百分之百。」換蕭練用不耐煩的語氣打斷含光。
他頓了頓,轉頭對如初說:「做不好就重來,沒什麼大不了的,別聽他亂發話威脅人。」
「就說個兩句也叫威脅?」含光冷笑:「要是威脅她能增加成功機率,我會讓你見識到什麼叫威脅,就是怕不但沒用還造成反效果,我才一路好聲好氣,只敢提醒她失敗的後果。」
自從專案計畫啟動之後,這種對峙場面已經發生過不只一次。如初相當懷疑含光的強硬態度不完全因為擔憂移除禁制失敗,也反映了他對自己與蕭練訂婚一事的不以為然。然而含光不肯明講,她也只好裝作不懂,之前幾次她還會出聲打個圓場,或者拉蕭練離開,但今天她實在累了,索性垂眼盯著地板,假裝沒聽見。
然而今天她才一低下頭,就見原本掛在貓咪樂園上的銀薰球慢慢滾了過來,而喬巴翹著尾巴跟在小球後頭,也輕快地小跑步進入起居室。
紫檀木地板忽地有些搖晃,帶動她整個人都產生輕微的暈眩感,如初正懷疑是否自己過去幾天都沒睡好,精神狀態不佳,就見麟兮撒開四個蹄子,轟隆隆追在貓後頭狂奔入室。
牠的體型像匹小馬,跑起來的聲勢卻絕不亞於一條迅猛龍。說時遲那時快,蕭練環在如初腰上的手一緊,腳下劍光閃動,瞬間抱住她飛到落地窗前。含光伸長手撈起肥嚕嚕的喬巴,一個大跨步輕鬆跳過沙發,直接跨到戶外。
唯一留守原地的是殷承影,他站在麟兮前進的路線上,在牠衝過來時攔腰一把抱住,然後整個人朝後方斜飛而出,仰躺在沙發上,身上還壓了一只伸出舌頭直喘氣的青銅麒麟。
下一秒,沙發旁邊矮几上的花瓶搖了搖,跌落至地面。
「汝窯!」如初慘叫。
「複製品。經過上次的教訓,現在全家的瓷器都換成複製品。」蕭練摸摸她的頭髮。
如初鬆了一口氣,目光落在地面上,又發出一聲悲鳴:「銀薰球!」
被踩得扁到不能再扁。
承影翻身跨坐在麟兮身上,伸手撿起薰球,瞧了一眼問:「這玩意哪來的?」
「國野驛的庫存貨。」蕭練答。
「我叫邊鐘再送半打過來。」含光取出手機,按下放音鍵,問如初:「夠不夠用?」
那顆銀薰球論年分是件古董,論手藝則是件藝術品,哪能用打來計算。如初趕緊答:「謝謝,其實再給我一顆就好了——」
「還會再被踩扁的,下次別尖叫,聽得我頭疼。」含光一邊翻手機通訊錄一邊不耐煩地打斷她。
鈴聲響了幾下,旋即被接起,邊鐘痛快地先一口答應,又提到廚房研發出了好幾款新口味的桃酥,有黑糖、抹茶跟椰子口味的,還有一款加了杏仁粒,用法國進口的麵粉,麥味極香,推薦一試。
整個爭執事件,最後以大家和氣討論該買哪些口味的桃酥作為收尾。就連蕭練都被說服了,選了一款無糖但加有核桃與燕麥片的桃酥。聽說這是入冬以來最受歡迎的款式,專門賣給愛吃甜食又怕胖的太太小姐們,沒想到居然意外合乎從來不吃甜食又不怕胖的蕭練的口味……
當然,和緩只在表面,每個人都緊繃著,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改變。
幾天後,如初果然收到六顆刻工與花樣都有些微不同、大小卻相差無幾的鎏金銀薰球,裝在一只手工雕刻著亭臺樓閣山水人物的檀香木盒裡,如同一件精美的禮物般放在她的工作桌上。
至於那個被壓扁的薰球——開玩笑,修復師連碎成百多片的青銅爵都能復原,修復一個被踩扁的銀薰球當然不是問題,正好順便練習紮圓箍幫器物整型。
只不過每當如初看到那個雕花鏤空的古董木盒,心裡總忍不住升起一股感慨,覺得這樣的日子太過奢華,她不太習慣,也不想習慣。
所有的紛紛擾擾,在表定的荊州鼎修復日,塵埃落定。
秦觀潮於早上八點半搭遊艇來到老家。如初一大早就穿上工作服在修復室門口等候。師徒兩人一起進場,秦觀潮鋸開一只豎耳,確認因內部腐蝕緣故,與豎耳相連的鼎緣部分略有變形,但不嚴重。他們於是分工合作,如初負責除鏽,然後把姜拓提供的補料填入腐蝕處,秦觀潮用他自製的小槌,一點點將形變部分敲回去。
修復工序推進得十分謹慎,雖然每一道步驟都已在事前經過討論與電腦模擬,當場他們還是先做小範圍測試,確認無誤後才敢真正全面執行。
如初可以從荊州鼎的外表來判斷修復的進程,但只有身負禮器傳承的秦觀潮,才能夠確知修復工作真正成功與否。
這是一種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感應,秦觀潮在之前就告訴她,到了這個地步,師父領過門,修行在個人。因此,足足一個禮拜的工作期,如初雖然自問每一步都做得夠踏實,心裡卻始終有點發虛,深怕沒拿捏好,一個對普通古物來說是正確的修復動作,卻會害得鼎姐再也醒不過來。
當豎耳與鼎身之間最後一絲縫隙完全消失之後,如初放下噴槍,推開護目鏡湊近了仔細觀察——肉眼可見之處,完美無暇,但,真的嗎?
她扭過頭徵求老師的意見。還沒開口,就瞧見秦觀潮嘴角微翹,流露出一抹欣慰中帶著感慨的笑容。
他朝她一點頭,說:「成了。」
如初哇地一聲跳了起來,杜長風衝進修復室,伸長雙臂一把抱住師徒兩人,含光、承影跟鏡子紛紛跨了進來,如初抱完了這個抱那個,忙得不可開交,一回頭見蕭練靠在牆壁上望著大家,眼角眉稍均是暖暖的笑意。
三天後,就輪到他了。
在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之前,如初已走到蕭練面前,一把抱住他,將頭埋進他寬廣而冰涼的懷中。
熱騰騰的眼淚淌下臉龐,如初一邊哭一邊不忘記警告蕭練:「不要問我為什麼哭,也不要安慰我。」
「懂,抱住就好。」他伸手環住她的腰,語氣裡竟還夾雜一絲笑意。
他為什麼一點也不緊張?
如初喃喃:「我其實對自己很有信心。」
「我也是。」他輕聲說。
「但還是好怕好怕。」
「我也是。」
連續兩個一模一樣的答案也太敷衍了。如初抬起頭,控訴似地說:「完全看不出來啊。」
「我有信心的時候不哭,怕的時候更不會哭。」蕭練一臉無辜地回答。
澎湃的心情忽地在瞬間止住,如初狠狠瞪了一眼蕭練,一把推開他,板著臉轉回到秦觀潮身旁。
當晚,大家在國野驛辦慶功宴,兼做秦觀潮的歡送會。如初吃到一半才知道秦觀潮的女兒原本在香港工作,之後會調到臺北,因此秦觀潮也打算先去香港逛逛,接著再搬去臺北住一陣子。她知道秦觀潮一直以來的心願就是,退休後跟女兒共度一段時光,然後全世界到處走走看看。如今眼看心願即將實現,如初也很替老師感到高興。
她趁大家酒酣耳熱之際,捧著果汁杯溜到秦觀潮身邊,舉起杯子說:「老師,我敬你,平安出行,旅途愉快。」
秦觀潮喝的是高度數白酒,看上去喝得有點多,臉都紅了。他跟如初碰了下杯,指著旁邊的兩個大紙箱,說:「我師父跟我的筆記,都傳給妳。」
這太珍貴了。如初一疊聲道謝,秦觀潮收回手,指指胸口,大著舌頭又說:「傳承這事兒,擱在心裡比放在腦子裡重要,要記住。」
「一定!」
秦觀潮瞇起眼看她,像是在評估這個弟子,微皺的眉頭彰顯出不盡如意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情。如初最不會應對這種場合,她還在絞盡腦汁想說些什麼讓氣氛不至於尷尬,卻聽秦觀潮問:「今天妳在修復室裡,有沒有瞧見、嗯,一棵樹?」
為了這次修復,杜長風特別將老家原本的修復室重新裝修,附帶也整理了周圍的庭園。雖然屋內為保持乾淨,連盆栽都不放,但戶外花木扶疏,小橋流水造景一應俱全。從落地的玻璃窗看出去,滿眼綠意,不要說一棵樹,幾十顆樹都數得出來。
「外面那些樹嗎?」如初問。
秦觀潮一怔,神情在瞬間變得有些不自然,但他揮揮手,說聲沒事,然後又將話題帶回那箱筆記,指點她在研讀時還應該搭配哪些書,這個話題隨即被如初拋諸腦後。
這頓晚餐稱得上是賓主盡歡。離開餐廳前如初又跑到秦觀潮身旁,請老師如果到臺灣一定要通知讓她來招待。
秦觀潮醉醺醺地答應了,如初跟著他一起跨出門,忍不住低聲再問:「老師,我們這次修復,真的成功了吧?」
「那當然。」秦觀潮順手在她頭上敲了一下,口裡嘟嚷:「妳個小兔崽子還敢懷疑我?」
他真的喝醉了。如初單手抱住頭,傻笑著又問:「那鼎姐什麼時候會醒過來?」
「一個月?十個月?一年?十年?這誰能說得準,他們畢竟不是人,我們也不是醫生。」
這句話秦觀潮說得挺大聲,然而並未引起任何驚訝的目光,他說完後步履不穩地往下踏一階,身子晃了晃,杜長風伸手扶住他。如初停在原地,不敢置信地朝身旁的蕭練望去。
他先微微一怔,緊接著會過意來,伸手環住她,發出一聲嘆息。
「你一直知道?」她耳語似地問。
「我以為妳早就知道。」他輕聲回答。
所有的喜悅如退潮般消失得一乾二淨,胸腔被鋪天蓋地的恐懼填滿,壓得如初喘不過氣來。
是的,她早該知道,或者最起碼早該提出這個問題——就算移除禁制的手術能成功,他何時會醒過來?
但,她偏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