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費迪南.馮.席拉赫現年四十八歲,在柏林擔任刑事辯護律師,著有《罪行》《罪咎》《誰無罪》《犯了戒》,均為國際暢銷書,且改編為電視電影、舞台劇,甚至音樂會。
首部長篇小說作品《誰無罪》,書中敘述一樁謀殺案,一名義大利模具工人殺死了德國大實業家。年輕律師接下了辯護工作,而被害人竟是他摯友的祖父。他也發現那位長輩必須為戰時槍斃義大利游擊隊一事負責。不過,這本小說的真正主題在於德國人的第二重罪過,是戰後司法界在處理納粹犯行時的醜聞。馮.席拉赫提出一個問題:孫輩這一代的人該如何面對祖父輩的罪過?
他自己的祖父巴度爾.馮.席拉赫在一九三一年擔任納粹的青年軍領袖,一九四一年起擔任第三帝國的維也納總督,負責驅逐維也納的猶太人。一九四六年,在紐倫堡大審中,他由於違反人性的罪行而被判處二十年徒刑。巴度爾.馮.席拉赫於一九七四年死亡。
「你就是你」
我祖父出獄時,我還是個小男孩。當時我兩歲。我們住在慕尼黑的史瓦賓區,是一棟建於十八世紀的漂亮屋子,屋子上爬滿長春藤和野葡萄藤。歪斜的走道,碎裂的石板,入口的門卡住了。那是通往外頭鋪石道路的深綠色大門,屋子後面是玫瑰花叢構成的迷宮,還有噴泉、愛神的裸體雕像,但他手裡只剩下弓,箭早已消失無蹤。
我不記得祖父被釋放的事。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來自別人的述說,來自照片和影片。我父親和他的兄弟駕一部黑色的汽車去監獄接他,媒體為了這一天已特別在監獄門前搭建看台。我父親穿著一套合身的深色西裝,年輕的姿態顯得有些局促。我祖父很瘦。再來是攝自慕尼黑我們家院子裡的畫面:《明星週刊》發行人亨利.南恩坐在他旁邊,坐在院子裡一張舊鐵椅上,進行頭幾次長篇訪談,我們一家人則遠遠地站在後面的一棵栗子樹下。我祖父說得很慢,帶著奇怪的口音:威瑪一帶的口音。如果去聽那個時代的訪談,不禁會皺起眉頭,因為大多都有著口音—希特勒御用的建築師施佩爾就是操著一口巴登邦方言。當時大家都說我祖父「出口成章」,但那根本是胡扯:記者的問題是事先講好的,他已經把答案練熟了。然而,我祖父說的話沒有一句是我能夠理解的。
我四歲時,我們搬到斯圖加特附近,住進我母親的娘家。不久之後,我祖父也搬了過來。我們住在大園子裡,那是我外曾祖父在一次大戰之前建造的:一棵棵高大的老樹、一棟有列柱和露天台階的屋子、幾座池塘、一塊苗圃。父親和我一起釣魚,也帶我打獵。那是個自成天地的世界。大多數時候我都是一個人。對於祖父的種種,我依舊模糊不清。他蒐集了很多手杖,有些手杖裡嵌著燒酒酒瓶或是時鐘,其中一支手杖還藏了一把鈍頭劍,另一支看起來像是童話故事裡小矮人穆克的魔法手杖。
每天我們會散步到園子外的小書報攤。他必須慢慢地走。在監獄裡,他的一隻眼睛因為視網膜剝離,幾乎瞎了。有時候在街道上會有人跟他攀談,但我不喜歡那樣。我們每天都玩九子棋,每次他都用同樣的招數贏我。後來我想了很久,直到我明白他是怎麼贏的。但在那之後,他就不再跟我玩了,當時我大概五、六歲。在我們家,大人不太跟小孩子說話。那樣也好,我們不受打擾,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然而某種東西始終纏繞著我,某種我無法解釋的東西。我跟當地的孩子以不同的方式成長,跟他們幾乎沒有接觸。那些事物對我始終很陌生,而我從來無法感到自在。我無法向任何人訴說這種感覺,也許這種事小孩子從來就說不出口。
在家裡,沒有人會說「監獄」,提到時就只用地名「施潘道」來稱呼。可是有一次,我聽見一個訪客說我祖父被關了很久。那令我很興奮,因為我讀過一本關於海盜德雷克爵士的書。我很佩服德雷克的冒險故事,他常常被囚禁。我問過母親,祖父究竟做了些什麼。我不記得她說了什麼,只記得她給了我很長的解釋,都是我不懂的字眼,也還記得她的聲音跟平常很不一樣。想必很糟吧,我心想,也許是個詛咒,就像在童話故事裡一樣。
突然,他就這麼走了,沒有跟我道別。過了很久以後,我才得知他想獨自生活。他搬到摩澤爾河畔一間小型膳宿公寓。在牢房裡生活了二十年之後,他大概很難面對一切。在他死前不久,我還在那裡再見過他一次。那一天我直望著那條河流和山坡上的葡萄園,還有那兒的一頭驢子,牠不停地齜牙咧嘴。我祖父是個戴著眼罩、一個我不認識的老人。我想不起來那一天他到底有沒有跟我說話。他囑咐在他的墓碑上寫著:「我是你們當中一員。」很可怕的一句話。
十歲時,我進了一間由耶穌會教士所創辦的寄宿學校。當然我年紀還太小,但也勉強能夠適應,因為我們的年紀全都太小。我們拿到郵局存摺,裡面存著我們的零用錢,一個月四馬克。每個月的頭一個星期一,神父把存摺交給我們,我們就去郵局領錢。每一次都大排長龍,那個郵局職員還是用手寫的方式登記金額。第三次還是第四次的時候,他打個手勢叫我到前面去。他說他認識我祖父,說話時眼睛閃閃發亮。他說從今以後我可以不必排隊,直接去找他。我跑開了。那天下午,一位神父試著向我解釋什麼是納粹主義,我祖父做了什麼,還有他為什麼坐牢。事情還是令人迷惑,聽起來像《魔戒》作者托爾金筆下的故事,充滿奇異的生物。
十二歲時,我頭一次明白他是誰。在歷史課本裡有一張他的相片:「帝國青年軍領袖巴度爾.馮.席拉赫」。那幾個字仍歷歷在目:我的姓氏果真出現在教科書裡。在另一頁上有一張克勞斯.馮.史陶芬堡的照片,下面寫著:「反抗運動鬥士」。「鬥士」聽起來好聽得多。在我旁邊就坐著一個史陶芬堡家族的小孩,跟我一樣是孫子輩,我們直到如今都還是朋友。當時他知道的也不比我多。
又過了一段時間,課堂上才講到納粹主義。當時我們那一屆也有一個男孩出身施佩爾家族,另一個來自里賓特洛普家族,還有一個出身呂尼克家族。戰犯和反抗者的後代,全都坐在同一間教室裡。我第一次深深愛上的女孩是維茨勒本家族的人。彷彿歷史是一回事,我的人生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後來在家裡,我會跟每個家人談論那個時代。沒有祕密—有這樣一個姓氏的唯一好處或許是什麼事都隱瞞不了。我們不斷地討論,一個叔叔後來寫了一本談我祖父的書。我始終不明白祖父何以成為那樣的人。他哥哥卡爾在羅斯萊本就讀寄宿學校時自殺,死時十八歲。據說他承受不了德皇退位一事,但他死時,桌上攤放著一本佛祖語錄。他姊姊羅莎琳德後來成了歌劇女高音。他父親是「威瑪劇院」的總監,他母親是美國人。我有一張她的相片,一個美麗的女子,頸子修長。她的祖先搭乘「五月花號」移民美國,一位是「美國獨立宣言」的簽署人之一,另一個還曾任賓州州長。席拉赫家族裡出過法官、歷史學家、科學家和出版家,大多數在政府任職,四百年來這個家族的人都寫書。我祖父在這個富裕市民階層的世界裡長大,一個備受呵護的柔弱孩子。在幼年的相片上他看起來像個女孩,五歲以前他只會說英語。認識希特勒時他十七歲,十八歲時他加入了納粹黨。一個會在晨間慕尼黑「英國花園」騎馬兜風的大學生何以傾心於空洞刺耳的詞藻?那些粗暴之徒、剃光的粗壯後頸和地下室的啤酒屋為何會吸引他?他喜歡在文章裡提起歌德,請作曲家理查.史特勞斯當自己兒子的教父,為何他沒有在納粹焚書之際就明白自己跟野蠻人站在同一邊?因為他野心太大?個性太不穩定?太年輕?而這又到底有何重要?據說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是怎麼了?」一個好問題,可是沒有答案。
後來我上大學時,讀遍了有關「紐倫堡大審」的文獻,試圖理解那個時代的運作機制。然而,當事情涉及自己的祖父,歷史學家的解釋毫無用處。他去「維也納歌劇院」,坐在包廂裡,儼然是所謂的「文化人」,同時他卻下令封鎖火車總站,好把猶太人運走。一九四三年,他在波森聽過希姆勒關於殺死猶太人的祕密談話,他絕對知道他們遭到殺害。
別人向我提起他的次數多得數不清,以你想得到的各種方式:坦率、無禮、憤怒、欽佩、同情、激動。有人威脅要殺我,更糟的也有,糟到令人難以承受。然而,當我想起維也納,這一切都變得無所謂,變得無足輕重。如今,在我的新書《誰無罪》訪談中,我又被問起他的事。對方想知道如果不是冠著這個姓氏,我的人生是否會有所不同?我是否會選擇不同的職業?我是否是為了他的緣故而探討罪責?這類的問題想來無可避免。那些記者維持著禮貌,但也覺得我的態度有點奇怪:如果採訪過於偏重在我祖父身上,我一概拒絕受訪。他們覺得我在迴避,事實也是如此。我無法回答那些問題,因為我不認得他,也無法問他,而且我不了解他。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這是我頭一次寫他,也將是最後一次。
在法庭上,罪行受到調查,法官審查是否確實為被告所犯,然後裁量他的罪責。大多數被判刑的人跟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他們一時失足,脫離了正常的社會,以為自己的人生走投無路。一個人會成為犯案者還是被害人,往往只是出於巧合。情殺跟自殺有時只是一線之隔。
我祖父所做的事卻完全不同。他的罪行有組織、有計畫,冷血而且精確。那些罪行是在書桌上計畫出來的,有相關的備忘錄和商談紀錄,而他一再做出了抉擇。當時他說,把猶太人從維也納運走是他對歐洲文化的貢獻。在他說過這種話之後,任何更進一步的問題、心理分析都是多餘。有時候,一個人的罪過太大,以致其餘的一切都變得無足輕重。當然,當時的政府本身就是個犯罪政府,然而這無法替像他這樣的人脫罪,因為這個政府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我祖父並非撕破了文明的薄薄外衣,他的抉擇並非出於厄運、出於巧合、出於大意。如今在刑事訴訟中,我們會問:被告是否自覺到他所做的事?是否還能理解他所做的事?是否還能夠分辨對錯?在我祖父身上,這些問題都很快就有了答案。他的罪過特別沉重:他來自一個幾百年來都肩負著責任的家族,有幸福的童年,受過良好的教育,世界為他敞開,他大可選擇另一種人生。他並非無辜地犯下罪過。到最後,一個人的生活背景也決定了他罪過的深淺。
我祖父的罪過是我祖父的罪過。聯邦法院說:罪責止於一身。沒有株連家族這回事,罪過也不能被繼承,每個人都有權擁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在《誰無罪》裡,我寫的不是他,也不是他那一代的人。關於他們,除了那些已經被說過幾千遍、探究過幾千遍的事情之外,我一無所知。我對當今的世界更感興趣。我寫的是戰後的司法界,是做出無情判決的聯邦德國法院,寫的是那些法官,他們對納粹凶手所犯的每一樁謀殺只判處五分鐘的徒刑。這本書寫的是我們的政府所犯的罪行,寫的是復仇、罪責,還有那些我們如今仍舊不足之處。我們自認為很安全,但事情正好相反:我們可能會再度失去自由,從而失去一切。如今這是我們的人生,也是我們的責任。
在《誰無罪》的末尾,那個納粹的孫女問年輕的辯護律師:「我也是那樣嗎?」他說:「你就是你。」對於涉及我祖父的那些問題,這是我唯一的回答。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得到這個答案。
--本文摘自馮.席拉赫思辨散文作品《可侵犯的尊嚴》

-
因為我們不這麼做不行
我們究竟能否信任「群眾智慧」?我們可以決定「巧克力」是否該免費或付費購買嗎?憑什麼網路交換平台主張所有電子書都該免費下載?
-
《罪行》費納醫師
馮.席拉赫的書,被吳念真譽為是他這幾年看過最精彩的短篇小說,他在政大編劇課上至少講了三次,叫大家趕快去讀。這個故事也是德國ZDF電視台將本書改編成影集的第一集。
-
愛有多簡單:看《罪行》改編電影「罪愛你」
儘管人可能變得一無所有,儘管人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感到自己的心已經麻痺或已如槁木死灰,我們卻不會真的失去愛的能力。當我們願意重新去愛的時候,也就是我們重新接納希望進駐心中的時候,而那時,心也會重新甦醒過來。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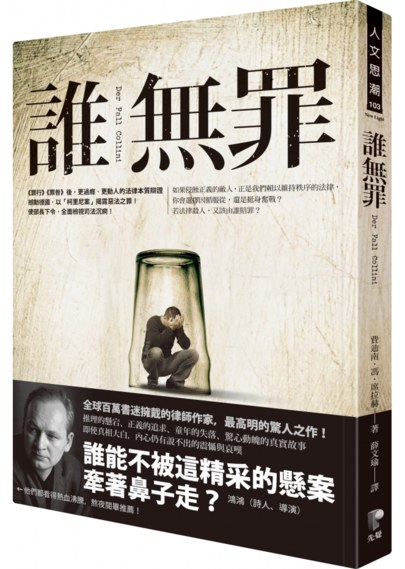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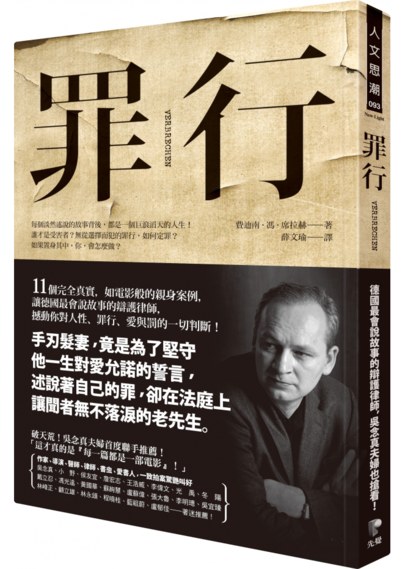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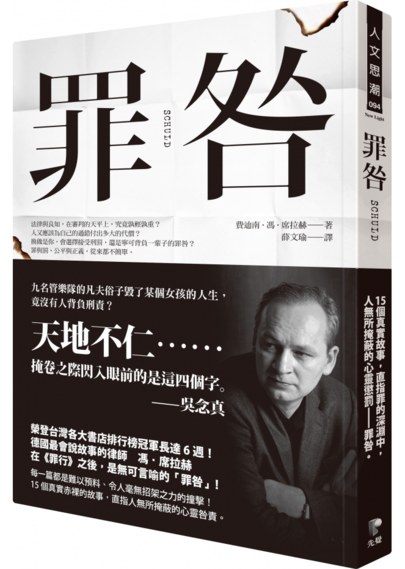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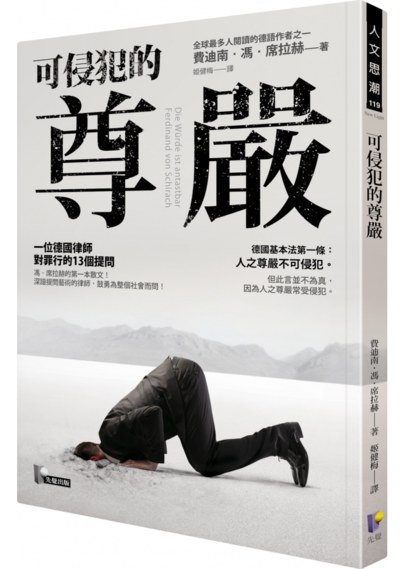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