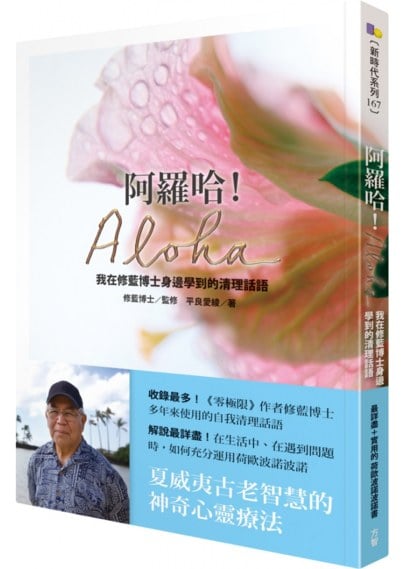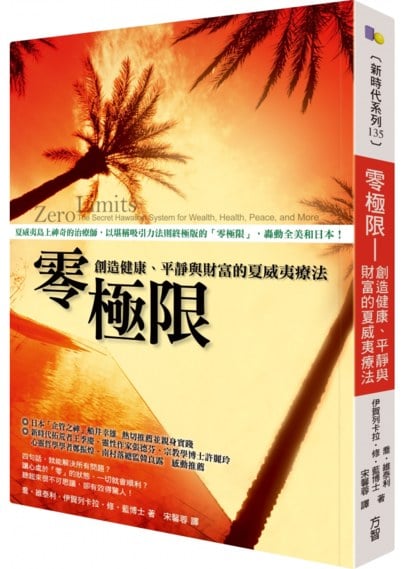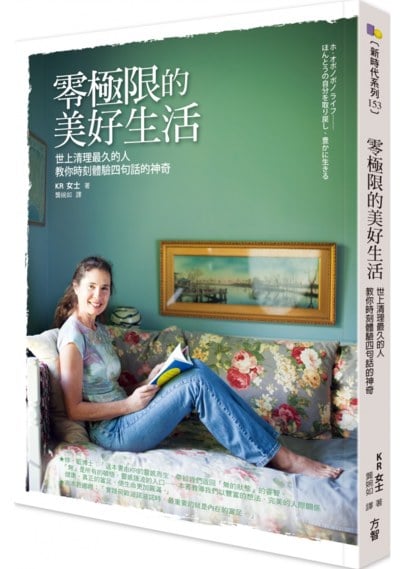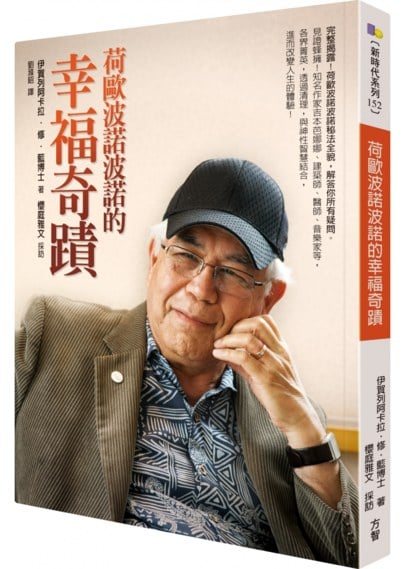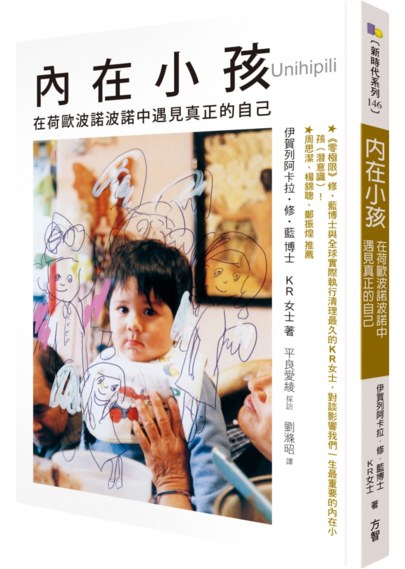某一年博士拜訪日本時,我們一起去了明治神宮的菖蒲園。
各種不同種類的菖蒲綻放著紫色的光芒,挺立於水池中。我們盡可能放慢腳步,靜靜地繞著水池走。因為菖蒲在那個季節盛開,池邊四處都擠滿了賞花的人。
我們在原地等了一下,讓剛才就排在我們後面的一整排人先走。這時我看見隊伍中有一個老婆婆。她的駝背非常嚴重,身材十分嬌小,很努力地跟著隊伍移動。接著,我聽見跟在她後面兩個歐巴桑之間的對話。
「好討厭喔,你看她的背彎成那樣,真的很難看耶。」
「這樣根本就只看得見地上吧,真不知道她來做什麼的。」
那一瞬間我心中馬上湧現很不舒服的感覺,希望老婆婆沒有聽到這些話。為什麼這兩個人要說這些令人不舒服的話呢?那一瞬間,我覺得非常難過又憤怒。
結果博士突然問我:
「你現在體驗到什麼?」
博士是聽不懂日文的,也應該聽不見那兩個人之間的對話才對。是不是我太情緒化、全身散發出憤怒的氣息呢?於是我老實地把自己的感受告訴了博士。
我把自己所見、所聞、心裡所想的,全部老老實實地告訴博士。一邊說的同時,我覺得自己似乎變得非常激動,一邊想著:「我所感覺到的應該是一般人很理所當然的情緒吧?這是很理所當然的感覺吧?」
當時我感覺到一種很想馬上擦拭乾淨的屈辱感。和博士說話時,我的臉上經常會表現出這種打從心底湧起的想法。
但博士只是一臉認真而嚴肅地繼續對我說:
「你怎麼知道嘲笑別人的人是否真的比較幸福呢?你又怎麼知道低頭流著眼淚的人真的沉浸於悲傷中呢?
「首先,我希望你了解,所有一切都是你所見的、所聽聞的。如果你在外在看見、聽見了悲傷,這些悲傷其實是存在你的內在。
「你看看那邊的樹,覺得那棵樹看起來開心嗎?還是看起來悲傷呢?樹是不會流眼淚的,樹也不會大聲笑,樹只是以生命、以自性的狀態存在那裡。不管是雨天、晴天,外在發生的事都不是問題,它只是活出自己的生命。
「當你看著那棵樹時,不管你覺得它美麗或醜陋,都和這棵樹沒有關係,那都是你內在發生的事。
「這個想法也適用於人,不管你看見的是誰、抱持著怎樣的情感、表現出怎樣的反應,都要先清理這些事情。
「你可以選擇進行清理,而非一直和記憶共處。清理之後如果有任何情感浮現出來,就再清理。你可以為這件事情負更多責任,因為主角是你自己。」
聽完後,我突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因為我總是很容易就陷入情感的漩渦。觀賞電影或紀錄片時,我的情感總是一口氣就湧現出來。雖然這並不是壞事,但聽了博士的話之後,我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玩瘋了、把東西丟得到處都是卻不整理的小孩。
「這位老婆婆是天使,是偉大的存在所創造出的完美存在。雖然她的駝背很嚴重,不管她的視線落在哪裡,說不定她都滿足於平靜之中。
「你覺得清理自己心中所見,能帶給多少人自由?你正負擔著非常大的責任唷。」
我可以用清理的方式來守護樹木,而不是用鋸子將樹枝修剪成我所希望的形狀,不必為了使它長得筆直而加上支撐木樁,也不會為了調整天候而將其放入溫室。但是我會進行清理,為了使這棵樹能盡情表現生命,為了使我能繼續欣賞這棵樹與其生命,我將繼續進行清理。
或許路過的人會說「這棵樹長得好奇怪喔」,或許過長的樹枝會勾到我的手,或許過了很久之後,這棵樹再也無法開出美麗的花朵、長出果實。
這時,我的心中應該會出現羞恥、悲傷或憤怒等情感吧。誠如博士所言,所有一切都來自我的內在。所以我必須自己清理這些自己丟出來的情緒,對每一個情緒說「謝謝你,我愛你」。
這麼做之後,即使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想像,卻也從這棵樹和我之間找出了許多沉重的想法,而我自己也能回復平靜的心情。就是這樣,我的內在小孩非常希望獲得自由,因為「平靜由我開始」。
在這同時,我發現了一件事。在兩個歐巴桑嘲笑駝背的老奶奶之前,其實我已經在心裡對老奶奶投射出這樣的語言「駝背得這麼嚴重,真可憐」。
在這個世界上,唯一有責任清理我所感受、我所見的,就是我自己。歐巴桑們說出來的這幾句話,或許就是為了讓我發現這件事。
最後博士告訴我:
「當然有時候也是需要行動的。針對出現在眼前的事物若湧現某些情緒,就進行清理。
「清理之後,就會在那一瞬間了解自己該怎麼做了。接下來就看你能不能誠實地表現出來。
「如果不知道該怎麼做,就再進行清理。清理完之後行動,然後再清理,就是這樣不斷重複。不管任何時候、看見了什麼,我都希望你能重新回到清理。
「為了做『真正的自己』,內在小孩的協助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內在小孩非常認真地在觀察你是否真正誠實。」
--寡言的修藍博士最多清理話語《阿羅哈!Aloha》











.jpg)
.jpg)


.jpg)